马明宗 | 丝绸之路儒学的研究价值与未来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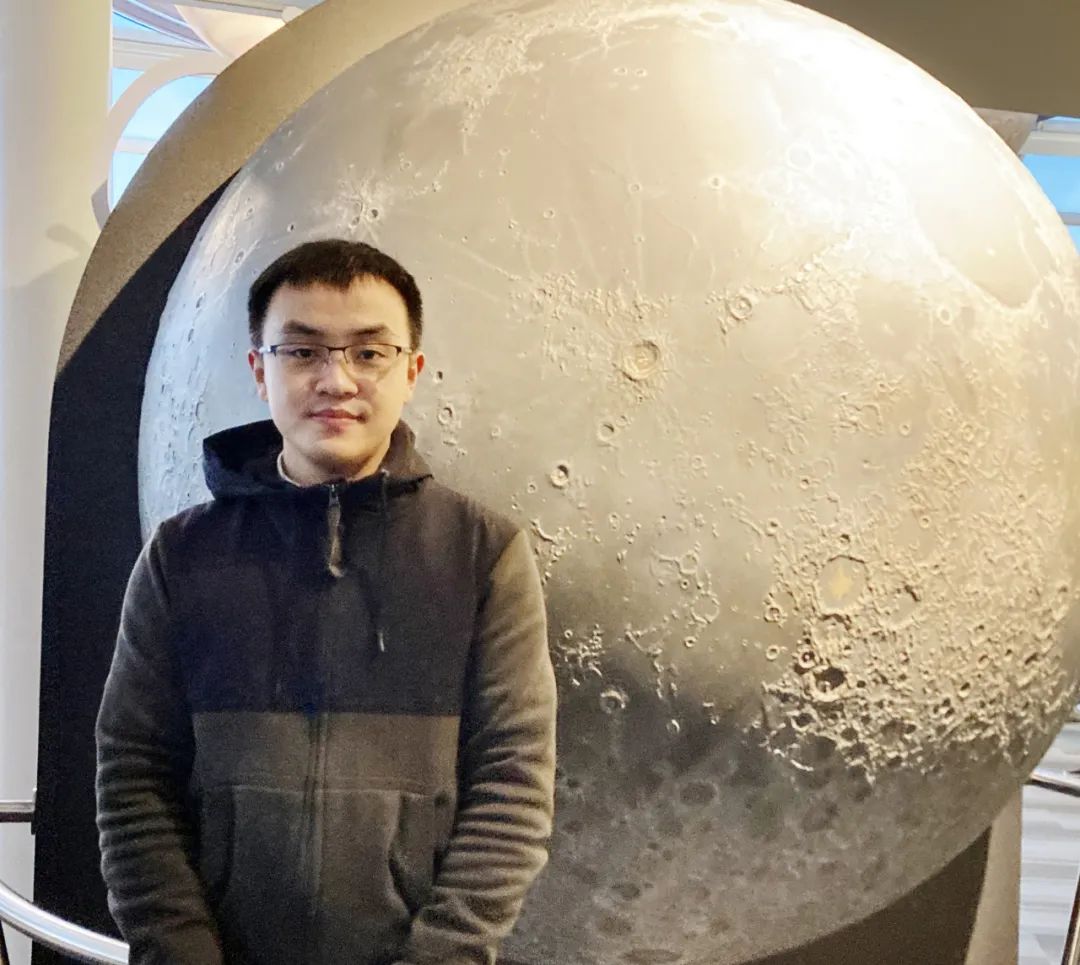
本文来源:《孔学堂》(中英文)2024年第3期。
摘要:丝绸之路是一条贯穿欧亚大陆的国际大道。在历史上,这条大道沟通大陆两端的经济、文化、政治,成为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脐带。在这条关系人类命运的枢纽上,不同的文化相互借鉴,不同的思想交流碰撞,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其中,儒学便是这条大道上思想交流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与以往学界的话语体系和关注重点有所不同,经过研究和剖析发现,丝绸之路上不仅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东传,还有儒学的西向传播。儒家文化正是通过丝绸之路影响周边国家,儒家文明正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存在才能长盛不衰。丝路儒学的传播和实践不仅是重要的历史史实,更是未来值得发展开拓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丝绸之路 儒学 价值 建设
作者马明宗,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简称“一带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re,缩写为BRI)。该设想的提出,旨在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和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融合。截至2023年,“一带一路”合作提议诞生十周年之际,我国已经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余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举办了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力地推动了“一带一路”交流合作。
纵观历史,“一带一路”上各个国家交流交往,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更不仅仅是世人所熟知的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商品,文化的交往与交流,思想的碰撞与交融才是丝绸之路带来的最宝贵的财富,才是人类历史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形成的重要推动力。就丝绸之路文化、思想交融交流的研究,以往的学者往往关注佛教的东传、基督教的传播、伊斯兰教的扩张、四大发明的西传等传统问题,而忽略了儒学这一中华民族精神内核通过丝绸之路的扩散与传播。儒学作为亚欧大陆东端意识形态的主体,诞生于人类思想迸发的轴心时代,不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深刻地塑造了东亚民族的精神内涵,而且进一步通过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影响着沿线国家的文化,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近代文明的成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因此,研究丝路儒学的历史,展望丝路儒学的未来,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还是我们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深刻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铸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要求。
一、丝路儒学的研究范围
要想探讨“丝路儒学”,就要先明确“丝路”的概念和范围。“丝路”是“丝绸之路”的简称。“丝绸之路”,其最初含义,是汉武帝时期以张骞为代表的使者向西开辟的“凿空”之路。“丝绸之路”的名称,最早是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其名著《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一书中提出来的,他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叫作“丝绸之路”。[1]1910年,德国东洋史学家阿尔贝特·赫尔曼(Albert Herrmann)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中主张,应“把这一名称的含义进而一直延长到通向遥远西方叙利亚的道路上去”,因为“叙利亚尽管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但也是其较大的市场之一,而且叙利亚主要是经由通向亚洲内地及伊朗的这条通道获得生丝的”。[2]赫尔曼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学者们的赞同。此后,“丝绸之路”的概念进一步扩展,成为从中国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欧洲通道的总称。[3]
需要强调的是,丝绸之路的主方向虽然是东西方向的,但是由于其所跨地域十分广阔,地理条件和历史情况千差万别,因此丝绸之路不会仅仅只有一条“路”,也不会是一条笔直的“路”。实际上它是由若干条道路东西相连、南北交错而形成的交通网,甚至不仅有陆路,也有水路。现今一般认为,广义的丝绸之路,主要包括穿越关中平原、陇东陇西高原、河西走廊、西域、中亚、西亚、南欧、北非的主道。其途经我国西北及中亚等地的绿洲地带,可称其为“绿洲丝绸之路”,因其又经过广袤的戈壁沙漠地区,可将此部分名之为“沙漠丝绸之路”。除此而外,还有穿越阴山、天山以北、蒙古草原等地的“草原丝绸之路”;穿越陇南盆地、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缅甸、越南等地的“西南丝绸之路(亦称南方丝绸之路)”及由中国东部沿海,尤其是从广州和泉州出发沟通东南亚、南亚、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4]后三条丝绸之路,在古代也扮演了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其波澜壮阔、久盛不衰的历史丝毫不亚于传统意义上的“绿洲丝绸之路”,并且,时至今日都在东西交流的大潮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所谓的“丝路儒学”,就是在这几条丝绸之路上交流、传播、碰撞、融合、发展的儒家经典、儒家学说、儒家思想、儒家学人,以及儒家历史文化遗迹。
就学界目前的研究来看,丝绸之路儒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一方面海上丝绸之路东亚一段儒学的研究已经相对充分,有专门研究韩国儒学历史的,譬如《韩国儒学史》(尹丝淳)、《韩国儒学史》(李甦平)等,还有专门研究日本儒学历史的,譬如《日本儒学史》(高田真治)、《日本儒学思想史》(三宅正彦)、《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刘岳兵)等。另一方面,西南丝绸之路儒学的重点——巴蜀儒学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譬如目前正在编纂的大型丛书《巴蜀全书》就对巴蜀儒学文献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目前还有《巴蜀经学文献通考》业已编成,正待付梓。此外,部分丝绸之路上的出土文献中的儒学文献也有一定程度的整理,譬如敦煌文书中的儒家经典就和佛教经典、道教经典一起被编入《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但目前丝路儒学的研究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对于丝绸之路儒学,学界虽然针对各个部分进行分别研究,但并未就“丝绸之路儒学”的整体框架构建学术体系,并未总结出“丝路儒学”的学术特色,研究处于“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其次,对于一些冷门问题关注太少,譬如琉球国的儒学、渤海国的儒学、蒙古高原的儒学、青藏高原的儒学、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儒学、东南亚的儒学等问题研究较少,当然这都是未能建立学术体系的缘故。再次,丝路儒学文献的整理不足,大部分研究皆未能脱离泛泛而谈的窠臼,未能从梳理文献出发,从实证得出结论,以材料论证观点。最后,对丝路儒学传播、交流和发展的历史阐释不够深入,未能深刻总结出儒学在外传过程中的变化,未能总结儒学与不同宗教、学术甚至地方文化的融合及其特色。这些都是今日丝绸之路儒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二、丝路儒学的发展历史
因为丝绸之路的多元性,所以丝路儒学的传播也具有多元性。儒家学说经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遍及东亚,对朝鲜、日本等国的影响至深至远,形成了东亚汉字文化圈,也就是东亚儒学文化圈。这段历史是人们古来所熟知的,学界也已经进行了非常充分的研究。[5]
除了儒学的东传以外,儒学通过绿洲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向西、向南传播,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向北传播,也是历史上儒家学术外传的主要路径。
从历史上看,儒学在绿洲丝绸之路上的早期传播,特别是儒学在西域段的早期传播,是与汉民族在西域的屯田和移民分不开的。从《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汉书·西域传》等文献的记载来看,早在汉武帝远征大宛的时代,就有一些疲惫的士兵留了下来。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文化向西域的传播,其一开始就内含着儒家文化的交流。早在汉代,儒家经典就在戍守边关的将士以及屯边民众中传播开来,在今天甘肃西北、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河流域,发现了肩水金关汉简、居延汉简等多批简牍,其中就有不少有关儒家经典,譬如《论语》《孝经》的残简;在更西的新疆,在罗布淖尔、楼兰尼雅遗址中也有汉代竹简本《左传》《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的发现。这表明,早在汉代,儒学就已经通过绿洲丝绸之路向西传播。
到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五胡内迁,中原人口大量流移,而西北凉州境,自武威至敦煌,再到高昌,成为西北重要的“避难地”。[6]这些移民一直以华夏文化为自己的最根本信仰,甚至视自己为晋之正统,虽然河西和西域屡易其主,但对汉文化的认同不忘初心。这正是儒学价值观念的影响所致。
正是与中原紧密的商贸联系和人口往来,使得儒学在绿洲丝绸之路上传播开来。《晋书》载,西凉庚子五年(404),西凉在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7]。由此可知,西凉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还有,在吐鲁番出土文书《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是关于西凉建初四年(408)三个秀才的对策,主持策试的主考官是西凉王李暠。策试涉及《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还涉及《战国策》《史记》等史学典籍,充分说明了当时吐鲁番注重经史的传统。另外,高昌也是丝绸之路上儒学传播的重地。《周书》载:“(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8]《魏书》载:“(高昌国王麹嘉)又遣使奉表……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以为博士,肃宗许之。”[9]儒家经典从北魏引进高昌,高昌王麹嘉居功至伟。除了研习儒家经典外,高昌还崇礼儒家圣人,将孔子等人画像挂在厅堂,《隋书》载:“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10]这些史料,都说明了孔子思想和儒家经典在西域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在高昌国时代,儒家文化的普及深入人心,不仅有正规的学校教育,还有大众化的知识普及。儒学不仅繁荣发展,还产生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高昌国的佛教寺院也讲授儒家的“孝”道,儒学与佛教逐渐融合起来。
以上这些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献,都充分证明了汉唐时期儒学在绿洲丝绸之路上持续而广泛的传播,并对西域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儒学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除了绿洲丝绸之路外,儒学也在西南丝绸之路上传播开来。西汉时期,汉武帝得知四川和印度、中亚之间早有连接的古道之后,遂令张骞以蜀郡(治所在今成都)、犍为郡(治所在今宜宾西南)为据点,派遣密使“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11],兵分多路探索去往印度的古道。虽然未能完全开通,但是也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南地区,甚至东南亚国家的交流、交往。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为成都,西线为牦牛道,或称为“灵关道”,从成都南下经过临邛(今邛崃)、青衣(今雅安)、窄都(今汉源)、邛都(今西昌),最后抵达叶榆(一说在今大理);东线为焚道,或称“五尺道”,从成都南下,经古道(今宜宾)、朱提(今昭通)、夜郎(今威宁)、古味(今曲靖)、滇池(今昆明)至叶榆(一说在今大理);东西两线在滇西交汇为永昌道,经永昌(今保山)、腾越(今腾冲)抵达缅甸、印度地区。西南丝绸之路除了向西连通缅印之外,还向南、向东经过昆明、文山、河江、宣光连通越南,并最终与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对接。[12]
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控制了滇池周围的广阔土地。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昆明晋宁区河泊所村发现了大量的简牍和印泥,其中有字简牍数千枚,简牍中还发现了《论语》的残片,这说明伴随着中央政权对国土的有效控制,必然会促进儒家学说的传播。至唐代,南诏国“劝民间读儒书,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13]。宋、元、明、清,云南地区的儒学一直不断发展。永平十二年(69),东汉政府在云南设立永昌郡,缅甸境内的一些国家和部落纷纷派遣使者与中国通好。此后,这些国家一直与中央政府保持官方和民间的商贸、文化、朝贡往来。清乾隆时期,清政府设立四译馆,其中就有缅甸馆,这一方面为中国培养了缅甸语人才,另一方面也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缅甸。乾隆六十年(1795),缅甸使者孟干来中国,曾把中国的《康熙字典》《渊鉴类函》《朱子全书》等大批古籍带回缅甸,促进了儒家文化在缅甸的传播。
越南也是南方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站,从成都出发的南方丝绸之路,一方面经永昌而西,与印度、缅甸等地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沿着云南的红河水而下进入越南,并最终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继续向南航行,沿中南半岛海岸线,进入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先秦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原地区言语不通,汉字真正大规模地传入越南是在汉武帝时期,越南学者黄高启在《越史要》中论述:“古昔我国人以布缠身,音话杂晓。武帝徙罪人杂居其间,复教我国人使知汉文,解北话。”[14]东汉的锡光、任延在交趾、九真担任太守时,在当地建立学校,推广礼仪,汉字就在当地传播开来。越南人将汉字称为“儒字”,将其作为官府和民间所通用的文字。随着汉文的推广和郡县制的推行,很多中原地区委派到越南的官员在当地开设学校。汉献帝时,交趾的李琴上书中央,希望通过举孝廉等方法推动越南人到中原任官,此举大开越南地区儒学教育的风气。汉末三国时期,交趾太守士燮精通《左传》《尚书》,曾为《春秋》作注,在其担任交趾太守时期,在当地开设儒学,“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15],推动越南地区的儒学教学和实践。越南史学家吴士连对此评论道:“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16]隋唐时期,越南地区的儒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当地风气“颇习文儒”,不少优秀越南学子参加科举,任职中央。越南李朝时期,太宁四年(1075),举行了越南脱离郡县之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三场”,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第二年建立国子监,“选文职官员识字者入国子监”,以培养王室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陈朝建立后,继续推广儒学,创办国学院,塑周公、孔子、孟子及孔门七十二贤人像,儒学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后黎朝建立,科举取士皆以儒家经典为本,洪德六年(1475)会试第一场四书共八题,《论语》三题,《孟子》四题,《中庸》一题,自选四题作文;五经各三题,独《春秋》二题。[17]阮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儒学,在民间兴办学校,雕刻印刷儒家经典,兴建文庙,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当然,除了缅甸、越南以外,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譬如泰国、柬埔寨,还有已经归属越南的占城,甚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都得益于这条丝路,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洗礼。
除了绿洲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外,草原丝绸之路也是儒学传播的重要路径。自古以来,北方少数民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南北朝时期的鲜卑人,唐代的契丹人、渤海人,后来的女真人都受到汉文化和儒学的浸润。蒙古人南下汉地之后,开始学习汉文化,并沿着草原丝路进一步将儒家文化传播到蒙古高原甚至北亚、欧洲。蒙古太宗窝阔台五年(1233),在蒙古高原的阿鲁兀忽可吾行宫,敕修孔子庙,之后又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立国子学、任用儒臣。蒙古高原上的上都路、应昌路、全宁路、净州路、集宁路等地都有孔庙和儒学学宫的设立。[18]大德十一年(1307),元朝政府在漠北设和林等处行中书省,置和林总管府,“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为和林行省左丞相”。哈剌哈孙十分重视儒学,“其在中书也,引儒生讨论《坟》《典》,至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为臣”。哈剌哈孙任职和林后,也肇修孔庙,为当地的儒学发展做出贡献。[19]
最能反映草原丝绸之路上儒学传播的是黑水城文献,此文献发现于内蒙古的额济纳旗,位于内蒙古的西部,是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在元代属于亦集乃路,其中的汉文文献中有《孝经》《论语》《孟子》《大学》《尚书》等,有的是初学者抄写,有的还有儒学教授的朱红批点。从这些文献之中,足以直观地看到草原丝绸之路上儒学的传播与发展。
整体来看,丝路儒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精神纽带作用,对东亚文化圈精神特质的成熟,乃至整个国际秩序的稳定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三、丝路儒学文献的状况
作为儒家学说的载体,文献是儒学传播、交流、融合过程的重要环节。儒学文献,既是儒学传播的媒介,又是儒学传播历史的见证。
正如丝绸之路展现出的多样性一样,丝路文献的传播和发展也存在几个大的板块,有草原丝路文献、海上丝路文献、绿洲丝路文献、西南丝路文献。就儒学文献方面来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海上丝路文献、西南丝路文献和绿洲丝路文献。
儒学通过海上向外传播,在两千年的时间中,几乎没有中断。在最开始的时间里基本都是东向的传播,主要是影响到汉字文化圈中的朝鲜半岛、日本和琉球等地。朝鲜半岛受到儒学的影响较早,早在汉代就曾纳入中国的版图,今天我们在朝鲜平壤的贞柏洞就发现了汉代竹简本的《论语》。根据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其中有《论语》中《先进》篇31枚竹简,涉及17章,557字;还有《颜渊》篇8枚竹简,涉及8章,144字。[20]这证明早在两汉时期,儒学文献就已经在朝鲜地区广泛传播了。后来的几千年间,朝鲜半岛不断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润,尤其是在13—14世纪性理学兴盛之后,朝鲜半岛还出现了许多本土的儒学大家,产出了不少本土的儒学文献,譬如郑道传《五经浅见录》《四书五经口诀》《入学图说》,李珥《大学谚解》《圣学辑要》《击蒙要诀》,李滉《四书释义》《朱子书节要》《启蒙传疑》等等,体现出强烈的在地化的性理学特点。[21]儒家学说在3世纪左右通过百济、高句丽等国继续东传传入日本,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移民的到来和隋唐时期遣唐使的交流,日本儒学发展日渐兴盛。到了江户时期,日本儒学发展到鼎盛阶段,林罗山有《大学抄》《大学解》《论语解》,伊藤仁斋有《论语古义》《语孟字义》《童子问》,荻生徂徕有《论语征》《学则》,等等,展现出浓厚的日本儒学特色。
巴蜀地区是西南丝路的起点,也是儒学发展的重镇。巴蜀儒学文献之中,尤其以易学最为耀眼,仅仅通过易学文献就足以窥见巴蜀儒学文献的发达。首先,易学是巴蜀儒学的重要特色,北宋程颐曾有“易学在蜀”之语,刘咸炘也提道:“易学在蜀,犹诗之有唐。”刘咸炘在《蜀学论》中所列举了许多巴蜀易学名家:商瞿(受业孔子,传其易学)、赵宾(授孟喜)、严君平(传扬雄)、扬雄(仿《易》作《太玄》)、任安(传孟氏易)、景鸾(传施氏易)、卫元嵩(撰《元包经》)、李鼎祚(著《周易集解》)、谯定(传程氏易)、冯时行(传谯定之学)、张行成(撰《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房审权(集百家《易》解成《周易义海》)、来知德(撰《周易集注》)等。除刘咸炘所举之外,巴蜀的知名易家和易著还有:晋代范长生,著《蜀才易传》,其经文在汉《易》和王弼《易》外,自成体系;宋代苏轼,撰《东坡易传》,融合《易》、玄及佛学;魏了翁,汉宋并重,删削《周易正义》成《周易要义》,还辑《周易集义》,汇集北宋理学《易》成果;元代黄泽,有《易学滥觞》;王申子,有《大易缉说》;赵采,著《周易程朱传义折衷》等;明代有熊过,著《周易象旨决录》;杨慎,著《经说》《易解》等;清代以后巴蜀地区的易学家更多,如李调元、刘沅、何志高、范泰衡、杨国桢、尹昌衡、廖平、段正元、刘子华、郭沫若等学者,皆有易学著述。[22]仅从群经之首的《易》,就足以窥见巴蜀儒学文献之丰富。在巴蜀儒学的辐射影响之下,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儒学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越南、泰国等中南半岛国家也深受其影响。从巴蜀地区向西、向南,儒家学说还影响到藏区、彝区,推动了儒家学说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在西北的绿洲丝绸之路上,与佛教东传同时,儒家学说也向西传播。尤其是因为西北地区干燥的气候条件和剧烈的人文变化,今天我们得以看到丝绸之路上众多的遗迹,尤为珍贵的是这些遗迹中发现了大量文献。譬如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吐鲁番文献,以及额济纳河流域的大批简牍类文献,其中不乏大量的儒家经典。从简牍到纸张,历经千年的黄沙洗礼,虽然不少已经是断篇残简,但依然能够窥见绿洲丝绸之路上儒学传播的兴盛。譬如,仅仅在敦煌一处,目前所能看到的《周易注》就有8种残本;《周易正义》1种残本;《古文尚书传》13种残本;《毛诗传笺》11种残本;《毛诗注》1种残本;《礼记注》4种;《礼记正义》3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19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节本》4种;《春秋左传正义》1种;《春秋穀梁传集解》3种;《春秋穀梁传经传解释》1种;《论语注》3种;《论语集解》10种;还有《孝经注》《孝经郑注义疏》《孝经疏》《尔雅注》等书若干种。[23]这些出土文献无不诉说着绿洲丝绸之路上儒学传播的兴盛、儒学交流的发达。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世界上原先各个独立的部分逐步地联系起来,丝绸之路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拓展。今日的丝绸之路不仅能够沟通欧亚,还能够到达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丝路之所及,儒学也自然生根发芽,儒学文献也自然遍地开花,不仅出现了翻译成当地文字的儒学文献,而且还诞生了本土学者研究儒学的著作。今天的儒学文献也不仅仅局限于东亚,以及靠近东亚的丝路沿线,在欧洲、美洲各国都有儒学文献的身影。
四、丝路儒学的未来展望
我们不仅要回顾历史、研究历史,更要展望未来、谋划未来。丝绸之路的儒学研究大有可为。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至今已有十年的时间。这十年中,在国家的支持下,古老的丝绸之路又重新焕发了新的生机。今天,研究丝路儒学,发展丝路儒学,是建设“一带一路”、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联合世界其他国家和文明,建设文化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要求。
要研究丝路儒学、发展丝路儒学就必须推动丝路儒学文献的整理。正如我们提到的,儒学借助丝绸之路得以传播和发展,推动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走向世界,而儒学文献则是儒学传播的基础和载体。因此,我们必须推动儒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一方面,推动绿洲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文献的整理,推动吐鲁番文献、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以及绿洲丝绸之路沿线上诸多零散出土简牍文书的整理,尤其注重这些文献中有关儒家学说、儒家思想部分的整理和发掘,在整理的基础上发掘其现代意义,推动“绿洲丝绸之路儒家经典整理”“绿洲丝绸之路儒学发展史”等相关专题的展开。另一方面,推动西南地区儒学的发掘和研究,巴蜀地区是西南地区的中心,古来就是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对内与云南、贵州、广西,对外与老挝、缅甸、越南、泰国,甚至是印度等都保持着相当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巴蜀儒学的影响下,这一地区形成了西南儒学的特色,并进一步影响到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儒学。因此,一定要注重巴蜀儒学文献的整理,推动“巴蜀儒学文献史”“巴蜀儒学文献通考”等专题研究。再一方面,注重整理东亚国家的儒学文献,加强与韩国、日本等国家儒学研究机构的交流交往,将东亚国家儒学文献的整理纳入中华文明圈的叙事框架之中。注重阐释东亚国家儒学文献的发展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调查研究儒学文献在东亚国家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历史,进一步对东亚儒学文献的现状进行普查,推动“东亚儒学文献通考”“东亚儒学文献提要”课题的进展。
要研究丝路儒学、发展丝路儒学就必须推动丝路儒学发展史、交流史的梳理。一方面,要摸清丝绸之路本国段的儒学发展史,推动“西北儒学史”“巴蜀儒学史”“云南儒学史”“贵州儒学史”“东北儒学史”“蒙古高原儒学史”等系列项目的开展。另一方面还要研究丝绸之路上其他国家的儒学史,譬如编纂“丝路国家儒学发展史研究丛书”,着重研究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还有欧洲、美洲等国家的儒学发展史、儒学文献史。再一方面,要推动丝路儒学交流史的研究,不仅要以国家、地域作为单元研究儒学,更要打破国家和地域的限制,研究儒家学术的交流史,譬如可以推动“中国—中南半岛儒学交流史”“中国—中亚国家儒学交流史”“中国—近代欧美国家儒学交流史”等专题的研究工作。
要研究丝路儒学、发展丝路儒学,就必须推动丝路儒学实体研究机构的建立。书院,是儒学发展和传播的重要机构,是儒学发展与传播的实体阵地。在历史上,书院的设立对儒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利用“一带一路”发展的契机,恢复“一带一路”上古已有之的重要书院,譬如成都的锦江书院、存古学堂,乐山的复性书院等,将这些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书院建设为推动儒学研究、传播的重要实体机构。另一方面,要仿照韩国遁岩书院、绍修书院、蓝溪书院等九处书院联合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举措,进一步推动中国书院,乃至“一带一路”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书院,在文化研发、遗产保护和联名申遗等方面的合作。再一方面,还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新时期的书院,推动书院与大学教育相结合,推动新书院的创立。最后,加强与海外科研机构、教育机构合作,让儒家书院走出国门,真正建立一批依托实体单位、发挥实际作用、立足真正研究、预期良好效果的国际书院。
要研究丝路儒学、发展丝路儒学就必须推动丝路儒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人才,是学术发展和继承的基础,没有人才,儒学的发展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西汉时期,文翁化蜀,是依靠蜀地学者,求学中原,才推动儒家学说的传播。魏晋时期,佛教东传,正是依靠丝路上无数的佛教传播者、佛经翻译者,才使得佛教在中原生根发芽。唐代的遣唐使,近代的留学生无不是如此。因此,推动丝路儒学的发展,必须加强儒学研究队伍的培养,尤其要注重具有学术本位、世界眼光、儒学信仰的人才队伍的培养。由此,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增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支持丝路沿线考察,全方位、高层次、多维度培养儒学学术人才。
要研究和发展丝路儒学,就要加快儒家经典的翻译。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国际交流合作的典范,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使用着不同的语言,汉语、吐火罗语、回鹘语、突厥语、波斯语等。无数的语言在此交流,不同的经典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只有在这样一条开放、自由、包容的丝绸之路上,才能形成文明、发达与兴盛的局面。我们要发展丝路儒学,就不能仅仅依靠某一种单一的文字,不能让文字的隔阂阻碍了思想的交流。因此,必须推动丝路儒家经典的翻译工作。翻译儒家经典和著作,不仅要翻译成文字使用人数较多的英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还要考虑到一些使用人数较少的文字语言,譬如马其顿语、塞尔维亚语、哈萨克语,等等。
研究和发展丝路儒学,需要完善丝路儒学学术体系的建立。从学术特点上来看,丝路儒学具备建设学术体系的可能性。首先,丝路儒学不同于传统的儒学研究,丝路儒学具有相当的融合性,牵涉到大量中外交流的历史。在交流交往的过程中,儒学产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和发展,无论是草原丝路上的儒学文献、海上丝路上的儒学文献,还是西南丝路上的儒学文献,都表现出与传统儒学文献较大区别的独特性。从另一方面来讲,学术体系是学术发展的依靠,只有形成自己独特且独立的学术体系,才能证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形成丝路儒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发展体系。
基于此,我们要全面地梳理丝路儒学的发展历史,整理丝路儒学的文献留存,恢复丝路儒学的学术遗迹,挖掘丝路儒学的特点,最终建立丝路儒学的学术体系。为丝绸之路儒学的发展、“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 编辑: 张益豪
- 统筹: 汪东伟
- 编审: 干江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