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文 | “道”的翻译有限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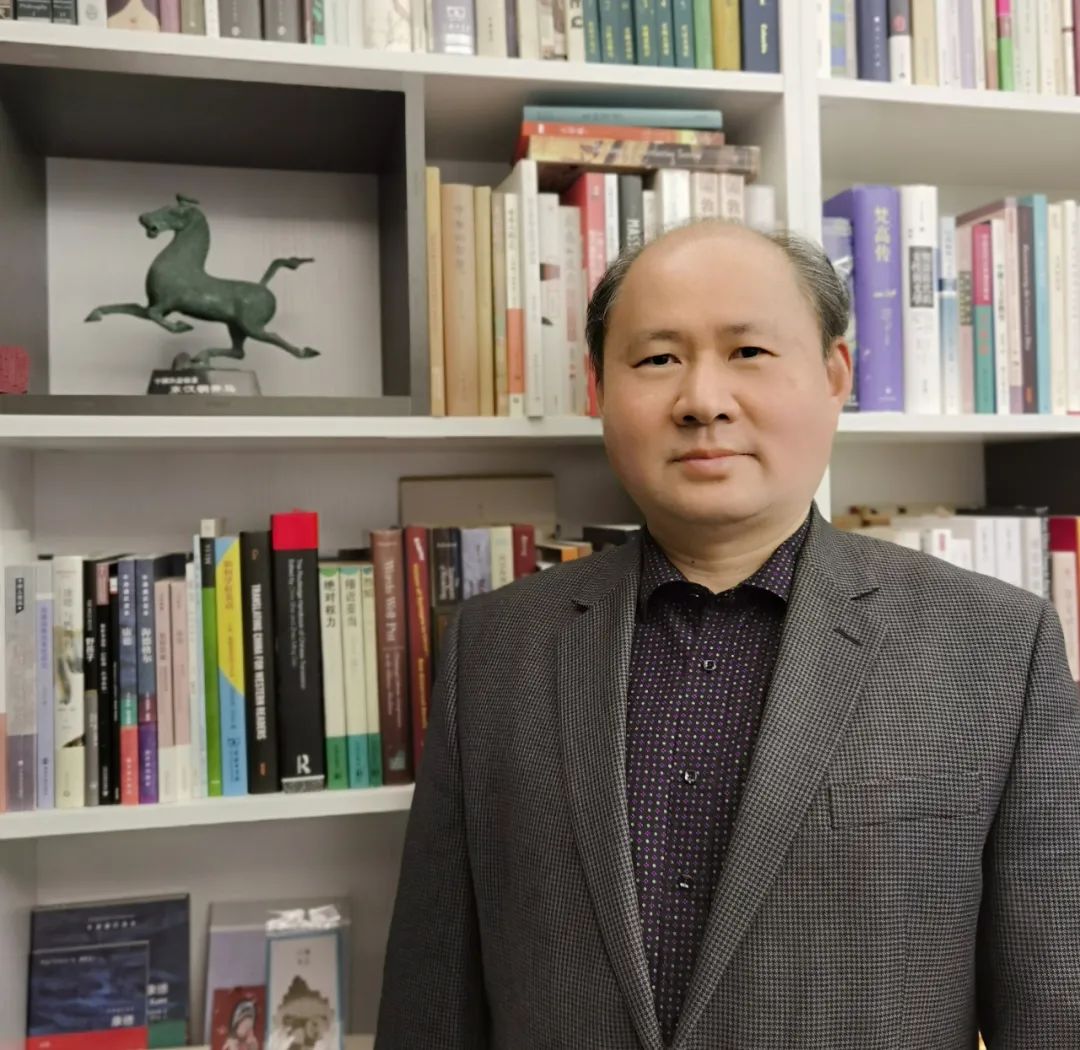
本文来源:《孔学堂》(中英文)2024年第4期。
摘要:言不尽意是语言的特征。中西哲学都会将不可言说问题作为探讨的对象。任何语言内部都存在着表达上的受限,是绝对性的、属于语言的绝对有限论,因此一个哲学范畴或概念很难独立地完成穷尽性表达意义的任务,只能不断地寻找替代者。这属于言内翻译模式。在中国的形而上学中,像“道”这样的终极性范畴有两个尝试性的替代词,即“自然”和“无”,作为其言内的对译词。如果将这三个范畴译成英语,它们同样会受到表达上的限制,这就是语言的相对有限论要探讨的问题。借助墨子的表达策略即“以名举实”“以辞抒意”和“以说出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语际间的相对有限性造成的不可译性问题。
关键词:道 自然 无 绝对有限论 相对有限论 翻译策略
作者刘华文,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老子的语言有限论
(二)庄子的语言有限论
一、语言有限论:绝对和相对
哲学的语际表达也就是翻译表达会受到语言有限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会体现在“道”这一中国哲学概念和西方哲学概念的互译可能性上。语言有限性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古典哲学翻译的策略,大多数的策略都涉及克服跨语言的限制。儒家、道家、玄学和禅宗分别发展了他们的策略来解决语言在表达上的受限问题,以便更有效地传达各自的理念。哲学在接受翻译的过程中也受到语际语言有限性的制约,能否参考儒家、道家、玄学和禅宗等中国哲学流派的语言策略去跨越语际表达的屏障,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在中国古典语言哲学中,对语言设限的意识根植于哲学流派之中。这种意识被理论性地表述为语言有限论(liminology),认为语言在不断试图跨越可言说和不可言说之间的界限。[1]言说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这个边界上发生的一场游戏。这个游戏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采用的是不同的语言策略。对于孔子来说,他所实行的是“予欲无言”(《论语·阳货》)的策略,抑或“述而不作”(《论语·述而》)的策略。对于庄子来说,其策略主要是所谓的“卮言”,即言语“就像高脚杯,‘夫卮,满则倾,空则仰’”[2],暗示了语言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禅宗的策略是“不说破”。这些策略是根据各自的哲学观念制定的。在中国哲学的跨语言表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克服与目的语相关的限制。如果在单语表达中有限性具有绝对性,那么翻译中又多了一层相对于原文语言的目的语即译入语在表达上的有限性。在用英语翻译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有必要根据汉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中所采用的语言策略来审视相对于汉语这一源语言的英语即译入语在表达上的受限问题。
语言有限性指的是人的意识、理性、哲学、科学、逻辑等所经受的在语言表达上的普遍或相对的制约力。[3]在翻译的语境中,特别是在哲学翻译的域界内,语言有限性指的是译入语在表达译出的哲学文本中的意义时所遇到的障碍,而这个意义是在源文本中表达出来的。有限性必然伴随着无限性。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相互伴随,使它们进入一种永恒的运动之中,或者说,“转化有限性或在有限处进行双重游戏”[4]。在有限与无限的相互作用中,有限起着替代者的作用,它受到无限的转化,正如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有限,或者每一个限制本身,都是开放给无限进行转化的。”[5]这说明有限或有限性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有限性的不稳定性在于它的可替代性。因此,“极限的无限替换是可能的”和“有限的无限补充是可能的”。[6]在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看来,有限与无限被在场与不在场所取代。然而,海德格尔声称,某物作为某物的在场是以一种使在场本身成为可能的缺席即不在场为条件的。解构的任务就是找回这种使在场成为可能的缺席或不在场。[7]德里达从根本上把这种观点推到了极端:“先验所指的缺席无限地延伸了意义的疆域和指涉游戏。”[8]
然而,在翻译语境中,原文有着抵制被译入语表达的制约力,不能轻易地被译文所取代。被呈现的文本必须在受限的前提下进行检验,这一受限操作被看作是跨语言进行的有限与无限之间的游戏。比如,以《论语》《老子》《庄子》《易经》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文本充斥着表层语言(即有限性)与深邃意义(即无限性)之间的互动。翻译的任务就是力图在译文中恢复这种互动关系。译者更多是在限度的边缘上有所作为,而不是也不可能完全克服这一限度。
德里达认为逻各斯在西方哲学话语中占据中心地位。他试图解构这一逻各斯中心主义。他于是制定语言策略来实现他的解构主义野心。这些策略包括双重否定、间接交流和诗性或启发性的语言。[9]概括地说,这些策略可以被归为延异(differing-deferring)的范畴。但解构主义者站在语言的立场上,试图拆除西方对语言的盲目自信。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就意味着解构语音中心主义。与此相反,道家的语言观是基于语言在本体论意义上就具有局限性这一前提,而不是基于语言能够完全表达意义这一认识之上。
儒家、道家和玄学的语言策略都带有解构主义的色彩。这一观点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哲学概念具有优越性,或中国哲学被迫与西方哲学进行类比,就像中国诠释学方法“格义”所做的那样。[10]然而,这种类比的方法可以使从比较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更有效力。
在《论语》中,孔子对“正名”的必要性做了如下说明: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 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孔子为什么发起正名运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的时代,错误命名是语言表达力不足的外在表现,是一种普遍现象。然而,孔子的正名论说明他对纠正误称持有积极的态度。在翻译中,译者很可能会为原名称的指代者提供一个名称。当他意识到对等词是一个不当用词时,则试图将其纠正过来。可以以“格义”为例,这是从东汉开始的佛经翻译家采用的一种方法。通过语义类比得到的概念对等词大多是误称,其中大部分在后来的时代都会被试图予以纠正。
道家关于语言限制的论点比儒家的更具穿透力。他们在对“道”这样的本体论范畴进行言说时,本质上怀疑语言的表现力。然而,这种不信任并没有削弱他们用语言表达本体意义的信心。道家制定了相应的语言策略如“强名”“希言”等,以不同程度的表达有效性应对语言的有限性。先秦哲学家关于语言有限性的观点及其克服语言有限性的努力可以归为语言有限论的范畴。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中尤以老子和庄子最为集中地代表了语言有限性立场。他们对语言的语义表达持否定或不可信的观点。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或增强语言的表达力,古代的哲学家们提出了对策,尽管这些策略的有效程度高低不一,但它们至少被尝试着用来表达哲学话语中的不可言说者。
二、老、庄的语言有限论
(一)老子的语言有限论
《老子》开篇就提出“道”在表达上的不可能性或不可言说性:“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老子对“道”与“名”的表达有着矛盾心态。在老子看来,对“道”与“名”的言说都是权宜之计。语言的有限性使人不能充分表达“道”或“名”。在可表达和不可表达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界限。这条界限始终在被试图跨越,但从未有人逾越到所期望的地步。这一有限论的观点呼应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凡是能说的都能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都必须保持沉默。”[11]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一个人只能谈论可言说的,而对于可言说边界之外的意义,则只能保持沉默。即使不可言说的意义在语言中出现,它也会遭受损失,被打折扣。说话者在说话时通常无法达到意义的圆满,并且一张口就会暴露出自己的无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德经》第五十六章)[12]真正懂得意义的人保持沉默。说话者不知道真正意义的原因,是他把“名”强加给“道”的:“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一个人要想从一个无知的言说者转变为一个博学的智者,就应该少说话,甚至保持沉默。老子意识到“道”的不可言说性,也只能强己所难地、临时性地称之为“道”。因此,他认为保持沉默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即“希言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三章)。这说明他对“道”的表达方式是以“道隐无名”(《道德经》第四十一章)这一有限性设定为前提的。他甚至更喜欢保持沉默,也就是“无言”“不言”或“希言”。
(二)庄子的语言有限论
先秦时期的另一位道家哲学家庄子在《庄子》一书中有一句话与老子关于知者与言者关系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即“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知北游》)。也就是说,知“道”的人不说出来,说出来的人并不真正地知“道”,所以说圣人的教导方式往往是什么都不说。庄子沿着这条论证路线,继续谈论语言的不足:“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默。”(《庄子·知北游》)唐代成玄英将这一说法评述为:“若论说之,则不至于道。”[13]于是,庄子呼应了老子关于语言有限性的观念,不过他没有老子那么激进,因为他制定了似乎更有效的策略来消除语言的束缚。他从不同于老子的角度阐述了语言的有限性。他认为,意义可以通过语言获得外化,但外化所得的意义不如原意义,即“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在这里,庄子对语言的表现力持否定态度,因为文字会侵蚀意义或使意义粗糙。由此可见,《庄子》间接表达了语言是有限的这一观点。庄子在其他地方也进一步迂回否定了语言表达力,如“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庄子·寓言》)。一方面,说不可说之意相当于是对不可说的一种抵抗;另一方面,用语言将不可言说的意义外化即表达出来将不可挽回地污损被表达的意义。因此,庄子也像老子一样,对语言的表达力有着有限性的认识。用来表达意义的言语一旦发出就逃不过失败的宿命。这种宿命的语言观在《庄子》中有如下表述:
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庄子·则阳》)
在这句话中,“居”也指事物所在的范围或边界。只要说出某件事,它就被限制在一个范围或领域内。物的虚空是无法命名和具体化的。如果它被说出,它就注定与真实的自己隔绝。成玄英对“可言可意,言而愈疏”的解释是:“可以言诠,可以意察者,去道弥疏远也。”[14]在语义上能说、能感知的则离道愈远。庄子的说法也是对语言有限性观点的呼应。然而,他的有限性与老子的有限性在激进程度上有所不同,因为庄子更乐观地设计了至少三种策略来克服语言的局限性,即卮言、寓言和重言。
虽然老子和庄子对语言的观念态度不同,但是二者的语言有限性均为绝对有限性:他们都认为本体论意义的不可言说具有普遍性。这种有限论是一种绝对的有限论:人类语言在表达意义上是有限的,甚至沉默比言语更有表达力。在翻译研究中,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一个经常被研究的问题,不可译其实就是不可言说。 在《不可译词词典:一部哲学词汇集》(Dictionary of Untranslatables: A Philosophical Lexicon)的序言中,主编芭芭拉·卡辛(Barbara Cassin)是这样定义“不可译”的:“谈论不可译决不意味着所讨论的术语、表达方式、句法或语法结构是绝对不可译的——不可译指的是人们针对某个不可译词语交替进行着译和不译。”[15]这里从不可译角度出发提出了译入语在表达源语内在意义方面的局限性,即译入语中没有最终对等的翻译。源语言对目标语言的限制是不可克服的。这样就从不可译角度出发,提出了译语在表达源语内在意义方面的局限性,即译语在翻译过程中没有最终对等对象。相对于源语言,目标语言在表达源语的意义时受到了限制。这种有限性不同于《老子》和《庄子》中所涉及的普遍有限性,而是相对于原文语言的有限性,所以属于相对的有限性,而不是绝对的有限性。
三、绝对有限性:言内不可译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们陷入了一种难以表达却又不得不表达的两难境地。他们把制定策略以摆脱困境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老子指略》中,王弼提出了两种指称终极存在的方式:“名”和“称”。[16]借助这两种指称方法所获得的是名称和指称,它们可以视为对等的等价物。但最典型的是,它们在这个意义上避免了相互指涉。这种排除概念相互替换的不可译性是在语言内发生的,是语言的绝对有限性造成的后果。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论述了这两种表达方式之间的区别:
名也者,定彼者也;称也者,从谓者也。名生乎彼,称出乎我。故涉之乎无物而不由,则称之曰道;求之乎无妙而不出,则谓之曰玄。妙出乎玄,众由乎道。故“生之畜之”,不壅不塞,通物之性,道之谓也。“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有德而无主,玄之德也。“玄”, 谓之深者也;“道”,称之大者也。名号生乎形状,称谓出乎涉求。名号不虚生,称谓不虚出。故名号则大失其旨,称谓则未尽其极。是以谓玄则“玄之又玄”,称道则“域中有四大”也。[17]
王弼在这段摘录中指出,“道”在语言表达上有局限性,但“道”有两种表达方式。他们是“名”和“称”。牟宗三认为名是客观的,称是主观的:“‘名生乎彼’,从客观;‘称出乎我’,从主观。”[18]这两种方法指明了言说“道”的两种取向。在王弼看来,“道”不能被客观性地命名,而是需要接受主观性的指定。“道”与“无”有关,没有形状和属性,无法在语言上识别或定义。在上述摘自《老子指略》的节选中,也有另一种对“道”的命名,即“玄”,一种黑暗或神秘,这出现在“‘玄’,谓之深者也;‘道’,称之大者也”的意蕴中。“玄”和“道”都是用命名的方式给出的。它们在语言内部是对等的,也是努力克服语言绝对有限性的结果。从表面上看,“道”不可言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从深层次上说,这些命名都因缺乏“道”的深远意义和语义上的不可穷尽性而有着缺陷。这正如所断言的那样,“因此,任何名称都将很大程度上无法捕捉它的真正含义,没有哪一个名称能真正地穷尽它的一切含义”,即“故名号则大失其旨,称谓则未尽其极”。作为克服绝对和相对有限性的结果,说话者或译者越接近名的命名行为,就越能克服语言的限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命名的客观描述超过了指定的主观强加,即让命名依赖于被命名物的客体化。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老子和王弼克服绝对有限性的方法可以用更具体的表达来理解,即墨子的“以名举实”“以辞抒意”和“以说出故”。[19]它们都可以归入“称”而非“名”的方法之下。但是,由于它们离“名”的距离不同,因此它们指称“道”这个表达本体论存在意义的范畴的资格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四、语言有限论和语言本体论
道家的语言有限论与本体论(ontology)或存在论(Being)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同时说明道家的语言哲学与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有着相当程度的呼应。[20]语言的有限论可以在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范畴内提出。从本质上讲,语言的有限性体现在非工具性、非对象性和存在(being)而非存在者(what is being)这三个方面。
如果一个人想克服语言的有限性,无论他想克服到何种程度,一般都会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说话者相信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意义的能力。但困难在于,对于言内和语际的命名来讲,所呈现的名称需要达到与其对应物相同的本体论地位,而不能仅仅是传递意义的一种工具。一个名称的存在性意义是确保其本体论地位的标准。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语言是“连结心灵、世界两方的‘媒介’‘工具’‘桥梁’‘通道’”[21]。此外,“这即是亚里士多德式对于语言与事物之关系的说明,也可以说是一种‘语言工具论’”[22]。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是要被人使用的。在这个意义上,是人在说语言。但是,海德格尔通过做出这个著名的声明颠覆了对语言作为工具的认识,从“人说语言”变成了“语言在说人”。[23]这样一来,语言就被撕下工具的标签而被赋予了本体论意义。安乐哲(Roger T. Ames)在阐发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观点时也谈到了语言的自主性:“这里的语言只是代表它自己,它把自己带到我们面前。”[24]他将伽达默尔的言论改写为:“语言掌控着一个世界的存在,而不能被工具性地和减约性地视为某些给定实在的单纯表征。”[25]在中国哲学中,像“道”“无”和“自然”这样的范畴,由于在言内和语际翻译中都带上了工具性意味,很容易面临被剥夺本体论意义的风险。语言本体地位的维持为语言表达设定了界限,同时也说明本体性语言是非指称性的。不幸的是,语言限制能否消除取决于如何给所指对象进行能指符号的匹配,而前提条件是语言符号必须指代一个对象或一个符号,指称不能为空,而且必须以具体对象为目标。被视为工具性和指称实体的语言需要被概括为一种存在者的语言(在海德格尔那里表述为Sprache des Seinenden),而不是存在的语言(在海德格尔那里表述为Sprache des Seyns)。表面上看,意义被表达了出来。但是,这样表达出的意义破坏了说话者试图要表达的本体性的存在论意义。
正如语言有限论所表明的那样,“因为能被命名的只是有条件的、具体的、可改变的事物,那隐藏和生成这些事物的事物是不能被命名的;而无名的东西是天地的起源和永恒的‘道’”[26]。可见,《老子》《庄子》等中国哲学经典中的语言是本体性的、非工具性的,因此指向的是“无”,尽管它也是权宜性的名称,但对存在本身的指涉是直接的。这些文本的作者总体上成功地命名了不可命名的东西。他们的语言是本体论的语言,或存在论的语言,而不是存在物的语言。一个经典文本的译者的任务是保留原文中固有的非工具性、非对象性和存在性。绝对的有限论妨碍了原始文本中这三个属性的实现。这些文本的翻译面临着两个挑战:一个是来自语言普遍具有的绝对有限性,另一个是来自相对于原文语言的译文语言的相对有限性。
一般来说,关于老子的道家的讨论最终会归结到“道”的范畴,就像关于庄子的道家和王弼的玄学的讨论分别归结到“自然”和“无”这样的范畴上。范畴是决定哲学归属性质的典型因素。下面将梳理“道”“无”和“自然”这三个范畴,以考察绝对有限性对言内表达的影响和相对有限性对翻译的影响。
五、言内翻译:对绝对有限性的克服
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提出了三种类型的翻译:语际翻译、言内翻译和符际翻译。[27]《老子》中的“道”是反映本体论存在(ontological Being)的原始名称。然而,老子并不满足于这种命名。他为“道”指定了其他名称,“自然”就是其中之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8]王弼在其对《老子》的评注中把“自然”重新定义为:“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29]他将“自然”等同于“无”这个名称,而王弼在《论语释疑》中又将“无”等同于“道”:
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30]
同样,“自然”也被认为是“道”的代名词。“‘朴’与‘道’在内涵上都是无为,无为就是任自然,故,这里的‘道’与‘自然’又是同义的。”[31]总的来说,“道”“自然”和“无”都是本体论存在的三个替代名称,而本体论存在是无法用语言充分表达的。对比之下,它们之间或多或少是有差异的。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着重揭示了存在或本体的三个层面中的一个。“道”可以被认为是本体论存在的原始名称,它是给存在强加一个临时名称的结果,是一种用来说明终极存在的工具。在对“道”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发现,它所代表的存在好比一条路线,可以把人引向最终的目的地,即它所包含的目标;或者说,在“道”的阐释能力中,取之不尽的语义潜力向无尽的阐释话语开放。“道”是一个范畴,其运作依赖于老子对它所要关联的本体存在的非工具性进行挑战。除了赋予“道”以工具性之外,“道”的使用者还将本体论的存在减约为一个实体,这就与本体的非实体性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道”在客观上是一个名称,在主观上是一个意向性地使其负载实在的称谓,所对应的是墨子的“以名举实”这种连接名与实在的方法。
与其说“自然”是本体的名称,不如说“自然”是“言”(词)或“辞”(术语或表达):“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32]这样就呼应了墨子表达意义的其中一种方法,即“以辞抒意”,用“辞”来表达“意”。王弼将“自然”视为“言”和“辞”,表明“自然”在其真正意义上并不像“道”那样是一个范畴的名称。墨子在《墨子·经说上》中,说道:“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这句话让人想起他的“以辞抒意”,即一个通过言语获得意义的过程,最终可以追溯到“心之辩”。周云之等人对墨子的这一论点评论道:“‘言’也即是‘辞’,都是用以表达一种思想的,而且这样的表达都是通过大脑的理性活动实现的(‘心之辩也’)。”[33]他们进一步认为,“《墨辩》的‘辞’不只是指语词,而且是指一种思维活动,具有判断的性质”[34]。同时,作为“言”和“辞”,“自然”更像是一个理性的判断,而不是一个孤立的术语。在其语义潜力中,“自然”具有本体论的维度,因为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判断的缩写,即“是其所是”。“自然”弃置了“道”的工具性,而“道”的工具性是有缺陷的,它有可能把存在减约为一个实体。“自然”强调了存在的本体论方面而不是实体方面。它的这一优点归因于其表达方式,即一种判断的形式。
“道”和“自然”在本质上是可以互换的语内等价物,只是它们适应不同的情况。无论如何,这两个范畴与“无”一起构成了一个等级体系,即“自然”比“道”更为高阶,这在《老子》中得到了证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这句话进一步表明,“道”低于“自然”。“自然”对“道”的优越性归因于“自然”比“道”更接近所预设的终极存在,因为“自然”保留了确保存在是存在而不是实体的前提条件。实际上,本体论的存在也有另一个名称即“无”,也应该是高于“道”的。“无”具有一种“自相矛盾”的特性:它向无数的语义潜力开放,同时也拒绝固守其一。它尊重存在对表达的抵制,而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挑战这种抵制的方式。“无”是一个非工具性的概念,因而也是一个与具有工具性的“道”不同的本体论概念。王弼认为的“道者,无之称也”很有道理。“‘无’在王弼哲学中的重要性,还表现在他明确把‘道’与‘无’等同起来。”[35]“无”就像“自然”一样,被置于高于或至少与“道”相提并论的水平。
“无”比“道”更根本,它既是“道”的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这个概念抓住了本体论存在的重要意义。因此,“无”起到了为存在奠定基础的作用,于是也就成了存在的终极因,用墨子的话说就是“以说出故”。《墨子》将“说”定义为“所以明也”,“说”是阐明存在之因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式推论”。[36]在这种情况下,“无”承担了“说”的形式,因为它唤起了相关概念之间的推论关系,然后构成了存在的“因”。它并不是指外界的一个实体,它是存在本身。综合评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既是最有效的,也是最理想的,它包含了“道”的三方面:非工具性、非对象性和存在而非存在者。
六、相对有限性及其对翻译“道”的影响
由于语言的绝对有限性,“道”最初未能充分表达它所要表达的对象。先秦时期和魏晋时期的一些哲学家努力克服这种局限性,为“道”提供了其他名称,即“自然”和“无”。这种努力是为了克服绝对有限性,因为它是在一种语言中进行的,或者用雅各布森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言内翻译。这种现象是绝对语言有限论的体现。相对于源语的表达力,由于翻译中的相对有限论,目标语缺少用来充分表达源语意义的词语。而这种语际之间表达的受限问题也需要解决,比如在将哲学文本从汉语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相对有限性与绝对有限性,同时结合老子的道家思想和王弼玄学中的三个关键范畴“道”“无”和“自然”的言内和语际的表达,尝试性地提出解决言内或语际的语言有限性的策略。
“无”应该有资格在语内取代“道”。王弼用这个词来弥补“道”的语义不足。“无”的单向可替代性在前提、背景和概念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37]“无”与“自然”一样,弥补了言内对应物“道”中不存在的本体维度。“无”完成了这一补偿任务,甚至被认为是“道”的一个合格的临时替代概念。但是,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在翻译王弼的《老子指略》时,把nothingness的“虚无”之意赋予了“无”。[38]这个对应概念将“无”减约为它的一个属性,因而未能呈现“道”的存在性。因此,nothingness之于其原文对应概念“无”就像“玄”“深”“大”“微”“远”之于“道”。[39]它们都是“无”或“道”的语义维度,只是各有其偏颇的含义,未能全息性地涵盖它们所共同对应的概念的含义,就如王弼所说:“各有其义,未尽其极者也。”[40]同时,nothingness作为“无”的对应词,是在相对有限论的范围内克服跨语言限制的结果,而其他五个字则是在绝对有限论意义上克服言内限制的结果。有鉴于此,nothingness并不完全有资格成为“无”的英文对应词,因为它的涵盖力和穷尽力尚未达到“无”所具有的水平。nothingness作为“无”的语际替代词所缺乏的涵盖性和穷尽性,就是王弼《老子指略》中以下这句话里的“兼”和“尽”:
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不兼则大殊其真,不尽则不可以名。[41]
同样,德国学者瓦格纳(Rudolf G. Wagner)在研究王弼的注释技巧时,将否定性(negativity)指定为“无”的英文对应词。在瓦格纳的论述中,“无”被标示为王弼对《老子》的评注中最激进的概念,并两次提到他有意将其翻译成negativity。[42]“无”作为王弼用来克服不可言说性的概念,当它看似要给出难以捉摸的所指时,立即取消了它试图指称的东西。它不仅否定了试图指称的东西,而且也否定了它自身。因此,如果“无”的对应词是negativity,它就被强制要求在自身中包含自反性。但是,negativity仅仅是指外部的取消,没有反身性的否定性。“无”原本是一个表达往来予取的概念,因为它缺席了它所呈现的东西。它是一种“去否定”(de-negation),这种否定不是导致肯定的双层否定。“无”的这种内在悖论性未能被吸收进negativity一词中。
王友如将non-being作为“无”的英文对应词。[43]虽然他没有直接证明这种翻译的合理性,但他在讨论庄子以否定性和悖论为特征的迂回表达方式时提到了这种替代性翻译。Non-being是由非(non-)和存在(being)组成的,由此可以推断,“无”在同时建构和解构自身。这一扬弃过程是由non-being的原文对应词“无”所固有的自我否定性和悖论性启动的。
“自然”作为同一语言中文内和互文中“道”的替代性概念,在《老子》和王弼对《老子》的评注中都起到了很好的置换作用。王弼在《老子》中经常提到“自然”,因为他很清楚“自然”在指称终极存在时能够克服“道”的有限性。瓦格纳意识到“自然”对“道”的可替代性在于这个词所固有的判断性,他在翻译王弼对《老子》第二十二章所做的一个注释“自然之道,亦犹树也”时,将“自然”翻译成That-which-is-of-itself-what-it-is。[44]作为“自然”的英文对应词的That-which-is-of-itself-what-it-is,第一个词“That”不是将“自然”转化为实体的外在化,它在语法上是将判断转化为一个名词,这个功能也由用以连接这些词的连字符来完成。瓦格纳在他对《老子》文本和对王弼的《老子》评注的翻译中以这种方式连贯地翻译了“自然”。他成功地将“自然”中固有的判断力呈现为一种态势,以消除相对有限性所设置的障碍,而“自然”这个概念恰好是老子和王弼用来作为克服语言的绝对有限性的手段。
相比之下,林理彰在翻译《老子》和王弼的《老子指略》时没有将“自然”统一地翻译成相同的英文概念,未能实现一致性。他为“自然”提供了三个英文对应词:the natural、naturalness和nature。实际上,林理彰在翻译“自然”时使用了更多的替代术语。在王弼的《老子》评注中,他将“此六者,皆陈自然,不可偏举之数也”译为:“These six [existence or absence, difficulty or ease, long or short, instrumental sounds or voice tones, highs or lows, and before or after] are all terms that express what is natural [ziran] and cannot be used with bias.”[45]如果从本体论上来解释,“自然”指的是一个过程,它最合适被表述为一种判断。如果它被表述为“什么是自然的”(what is natural),那么它就有可能被减约为拥有“自然性”(naturalness)这一属性的实体。在同一章节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王弼的另一个评注中也有“自然”,即“自然已足,为则败也”,林理彰将它翻译为:“That which by nature is already sufficient unto itself will only end in defeat if one applies conscious effort [wei] to it.”[46]“自然”最初是在被突出的核心位置,但在翻译中,它被降低到一个修饰语的地位。“先天的”(by nature)往往被解读为“后天培育”(by nurture)的反义词,这给人一种自然主义而非本体论的印象。对于瓦格纳来说,王弼的这一评注有这样的译法:“[The other entities’] that-which-is-of-itself-what-it-is already is sufficient [in itself]; interfering with it would destroy it.”[47]瓦格纳的翻译与他在处理“自然”时实现连贯性的努力以及他保持这个概念的判断属性的意识相呼应,但括号中加入“the other entities’”就把“自然”具体化为一个事物或一个实体的属性,使得这一呼应有了缺陷。
如果对比瓦格纳和林理彰对“自然”的翻译方法,可以看出瓦格纳对语境是不敏感的,因为他在翻译“道”的这个替代范畴时保持了一致性,而林理彰显然则是对语境高度敏感的,他为“自然”提供了不同的替代性翻译。执守和变通分别是他们在克服相对有限性的语际努力上所体现的特点。这两种诠释特征来自认知“自然”的两种倾向:一种倾向于“自然”的永恒性和起始性,另一种倾向于它的易变性、易受影响性和派生性。
七、进一步的思考
哲学翻译在语言有限性上面临着两个挑战:一个是绝对有限性,另一个是相对有限性。它们可以匹配以下语际间概念翻译方法中的一种:其一是王弼那里的名或称;其二是名、判断(即“辞”)或推断(即“说”)的运用,如墨子的“以名举实”“以辞抒意”和“以说出故”。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语言观与中国古代哲学家遇到的有限性障碍以及他们为克服这一障碍而制定的策略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针对意义的不可言说,他们在建构各自的哲学体系过程中甚至会创造新的概念来克服语言的有限性。
今天的译者倾向于对“道”“自然”和“无”进行音译。他们甘愿对超越语言的相对有限性无所作为。与其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失败,不如把目光放在其积极的方面,这就是老子所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48]的体现,抑或可以将音译看作是一种禅宗的语言策略。这一将道家和佛家融合在一起的思想流派所做的只是让说话者将想要表达的东西留在心中,也就是所谓的“不说破”。
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哲学典籍译释论”(项目批准号:23FYYB001)阶段性成果。
[1] 在王友如看来,“语言有限论的内涵就是对语言的限度予以相对化。要说明这种相对化的合理性就需要揭示语言限度的两边之间动态性的相互关系”。王友如的有限论并不局限于语言在表达意义时的有限性,还涉及如何克服也就是如何使语言的有限性相对化。参见Wang Youru, Linguistic Strategies in Daoist Zhuangzi and Chan Buddhism: The Other Way of Speaking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83。
[2] Wang Youru, Linguistic Strategies in Daoist Zhuangzi and Chan Buddhism: The Other Way of Speaking, 104.
[3] Wang Youru, Linguistic Strategies in Daoist Zhuangzi and Chan Buddhism: The Other Way of Speaking, 83.
[4] Wang Youru, Linguistic Strategies in Daoist Zhuangzi and Chan Buddhism: The Other Way of Speaking, 83.
[5] Wang Youru, Linguistic Strategies in Daoist Zhuangzi and Chan Buddhism: The Other Way of Speaking, 83.
[6] Wang Youru, Linguistic Strategies in Daoist Zhuangzi and Chan Buddhism: The Other Way of Speaking, 83.
[7] 参见J. Claude Evans,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es of Deconstruction: Derrida and the Myth of the Voi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xx。
[8]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280,转引自Evans,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es of Deconstruction: Derrida and the Myth of the Voice, xx。
[9] 参见Wang Youru, Linguistic Strategies in Daoist Zhuangzi and Chan Buddhism: The Other Way of Speaking。
[10] 苏源熙(Haun Saussy)认为格义更像是一种诠释技巧,而不是翻译技巧。但在将梵文佛经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更应该说格义同时产生了诠释和翻译的作用。参见Haun Saussy, Translation as Citation: Zhuangzi Inside Ou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1] Ludwig Witte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trans. D. F. Pears and B. F. McGuinness (London: Routledge, 2002), 3.
[12] Edmund Ryden将此句译为“One who knows her does not speak of her; / One who speaks of her does not know her”,见Edmund Ryden, trans., Daodejing, Oxford World’s Class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7。在Ryden对老子《道德经》的翻译中,“she”或“her”被特意用来指代文本中出现的不定指称。实际上,不确定的指称者更多的时候是文本中不可言说的“道”。
[13] 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28页。
[14] 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第516页。
[15] Barbara Cassin, introduction to Dictionary of Untranslatables: A Philosophical Lexicon, trans. Steven Rendall et. a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xvii.
[16] 参见王弼:《老子指略》,《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95—201页。
[17] 王弼:《老子指略》,《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197—198页。
[18]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8页。
[19] 《墨子·小取》:“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Ian Johnson翻译为:“Names are the means of ‘picking out’ entities; words are the means of expressing concepts; explanations are the means of bringing out causes”。见Ian Johnson, The Mozi: A Complete Transla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9), 620–621。本文作者则分别译为 “using name to signify reality”“using predication to let out intention”“using inference to verbalize entailment”。
[20] 参见钟振宇:《庄子的语言存有论——由晚期海德格尔哲学切入之探讨》,郑宗义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12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第93—115页。
[21] 钟振宇:《庄子的语言存有论——由晚期海德格尔哲学切入之探讨》,郑宗义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12辑),第97页。
[22] 钟振宇:《庄子的语言存有论——由晚期海德格尔哲学切入之探讨》,郑宗义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12辑),第97页。
[23]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 Albert Hofstadter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190.
[24] Roger T. Ames, Confucian Role Ethics: A Vocabula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234.
[25] Ames, Confucian Role Ethics: A Vocabulary, 234.
[26] Sun Zhenbin, “Discourse as a Method of Philosophy: The Ming-Shi Discourse as an Example”,方克立主编:《中国哲学和21世纪文明走向——第1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论文集之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8页。
[27] Roman Jacobso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On Transl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33.
[28] Ryden将这四个排比句翻译为“Humans imitate the earth; earth imitates heaven; Heaven imitates the Way; the Way imitates her natural self”。见Ryden, Daodejing, 53。其中“法”被放置在“人”“ 地”“天”“道”和“自然”中间,基本意思理解为imitate,即“模仿”。但鉴于“法”两边的范畴依次在升高,如果用emulate来翻译会更能表达这种递进的关系。
[29] 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4页。
[30] 王弼:《论语释疑》,《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624页。
[31] 康中乾:《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92页。
[32] 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楼宇烈校释,第64页。
[33] 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37页。
[34] 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第137页。
[35] 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0页。
[36] 参见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第151页。
[37] 参见蒋丽梅:《王弼〈老子注〉对“道”的诠释》,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第5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7—332页;甘祥满:《玄儒论“道”——以〈论语义疏〉为中心》,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7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4—284页。
[38] 参见Richard John Lynn, trans., The Classic of the Way and Virtu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Tao-te ching of Laozi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39] 参见王弼:《老子指略》,《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196页。
[40] 王弼:《老子指略》,《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196页。
[41] 王弼:《老子指略》,《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196页。
[42] 参见Rudolf G. Wagner, The Craft of a Chinese Commentator: Wang Bi on the Laozi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294;A Chinese Reading of the Daodejing: Wang Bi’s Commentary on the Laozi with Critical Text and Transl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123.
[43] 参见Wang Youru, Linguistic Strategies in Daoist Zhuangzi and Chan Buddhism: The Other Way of Speaking, 152–153。
[44] 参见Wagner, A Chinese Reading of the Daodejing: Wang Bi’s Commentary on the Laozi with Critical Text and Translation, 191; 以及Wagner, The Craft of a Chinese Commentator: Wang Bi on the Laozi, 292.
[45] Lynn, The Classic of the Way and Virtu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Tao-te ching of Laozi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54.
[46] Lynn, The Classic of the Way and Virtu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Tao-te ching of Laozi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54.
[47] Wagner, A Chinese Reading of the Daodejing: Wang Bi’s Commentary on the Laozi with Critical Text and Translation, 126.
[48]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09页。
- 编辑: 张益豪
- 统筹: 侯绍华 李沅栗
- 编审: 翟 佳 周之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