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平 王巧生 | 良知与知识关系视角下王阳明对《论语》的诠释——兼论经典诠释的边界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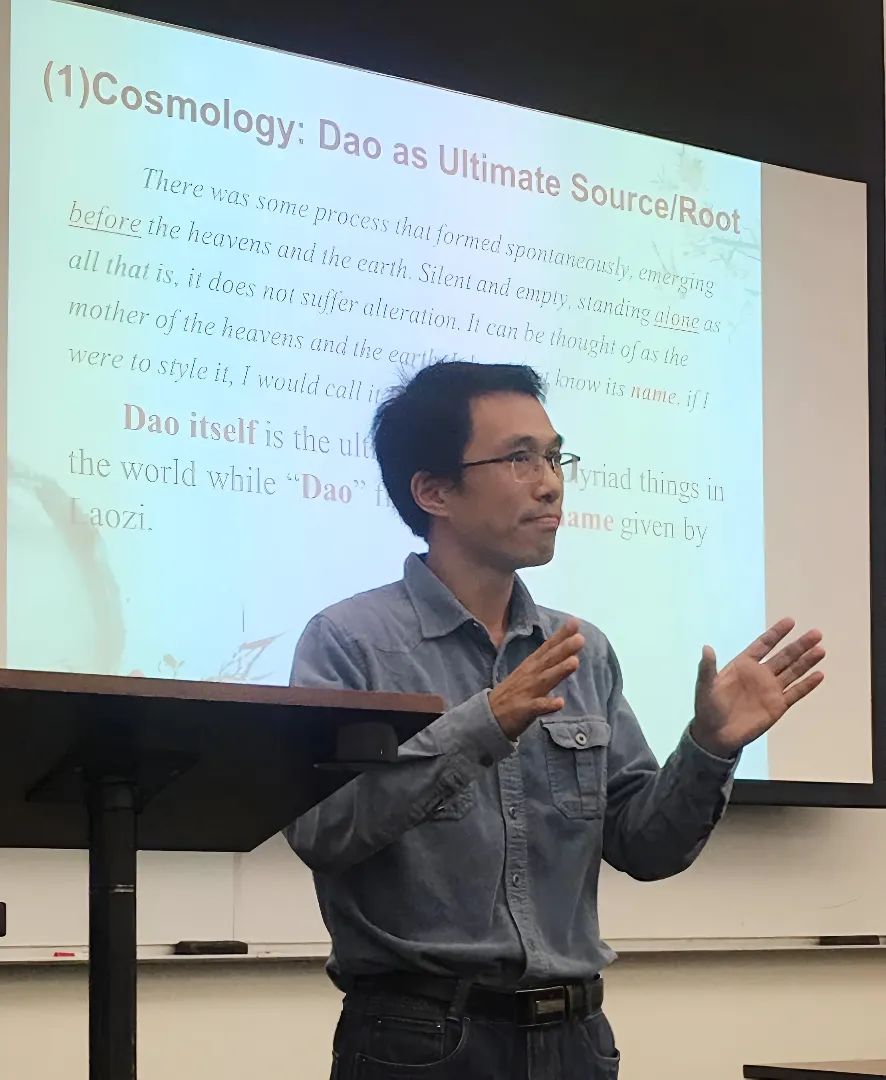
本文来源:《孔学堂》(中英文)2024年第4期。
摘要:王阳明在建构心学思想体系时特别注重引证早期儒家经典,其中《论语》被反复征引。王阳明在“心即理”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格物致知,为了证明向外物上探求天理是一种错误的道德修养路径,他区分了“良知”与“知识”,对《论语》中“多闻多见”“多学而识”“有知无知”等表述进行了重新解读,主张在闻见上做功夫不如在心体上用功;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学”只是在心上探求天理(良知),而致良知才是一贯之道;良知之外别无知,见闻之知都应当是良知发挥作用的结果;心之良知之谓圣,而知识无关乎成圣。从心学自身的体系来看,王阳明的这种诠释确立了良知的本体地位,以良知统摄知识,将德性涵养视为一切经验活动的根基,这对于阐发儒学的本质特征、彰显人的道德主体地位具有重要价值。然而,王阳明对《论语》的诠释是典型的“六经注我”,不少诠释罔顾经典文本的语境,以至于曲解原文,尽管阐扬出儒家的德性伦理思想,却忽视了孔子注重经验知识学习的主张。由此可见,经典诠释有其边界,在诠释古代经典时遵循语言学原则、历史情境原则、逻辑自洽原则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王阳明 《论语》 良知 知识 经典诠释
作者萧平,湖南师范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哲学系副教授;王巧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大纲
一、闻见上用功不如心地上用功
二、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
三、良知之外别无知
四、知识无关乎成圣
五、经典诠释的边界
中国古代哲学主要以诠释早期经典为“做哲学”的方式,这种经典诠释在宋明理学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程颐的《程氏易传》、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都是十分重要的经典诠释著作。然而,与宋明两代的大多数学者不同,王阳明几乎没有完整地注解过任何一本儒家经典[1],即便是《大学问》(又称作《大学或问》)[2],也是一种自问自答式的研究性著作,并没有对《大学》进行完整地注解或疏释,因而至少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经典注释。[3]《五经臆说》只有寥寥数条,很难说是一种著作。但是王阳明又确实对《大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尤其是融合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创造性地提出致良知。如果要证明“致良知”学说的正统与合法,那么就必然要从早期儒家经典中寻求坚实的文本根据,并进行重新诠释。王阳明在建构心学思想时原本就带有回归孔孟的色彩,故常常引证四书五经,其中《论语》是被引证最多的经典。[4]以《传习录》为例,笔者初步统计,全书共有70条语录[5]直接引用《论语》文本或典故101次,所引内容来源于《论语》的19篇92章。[6]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良知”(德性之知)与“知识”(闻见之知)之关系的视角考察王阳明对《论语》的解读,进而讨论经典诠释的边界问题。
一、闻见上用功不如心地上用功
王阳明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1747)从已有材料来看,他最早在41岁时就已经明确使用“良知”概念[7],如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7)这条语录明确将《大学》致知之“知”诠释为“良知”,将良知的充塞流行视为“致其知”,显然,“致良知”的思想已经蕴含其中。自此之后,良知作为阳明心学的核心概念日益凸显。[8]然而,要如何解读其他儒家经典中的“知”?能否诠释为“良知”?与此相关的就是“学”的诠释,既然“格物”并不是在“物”上穷究与学习道理,那么早期儒家经典中的“学”能否全部解读为“心上学”?面对各种质疑,王阳明首先对《论语》中的“知”与“学”进行了重新解读,《传习录》上卷记载:
黄诚甫问“汝与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贡多学而识,在闻见上用功,颜子在心地上用功:故圣人问以启之。而子贡所对又只在知见上,故圣人叹惜之,非许之也。”(37)
王阳明认为,子贡属于博学强记之人,因而主要在“闻见”上用功,即通过感官经验来获得知识;而颜回主要在“心地”上用功,“心地”主要是指心体、良知。很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王阳明认为孔子是让子贡去与颜回比较来激发他对本体的体认与探究,然而子贡似乎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点,仍然是从博闻强记上来回答。“非许之”的“许”字其实是针对朱熹的注解而言,朱熹注“吾与女弗如也”曰:“与,许也。”[9]意思是,孔子赞同子贡的说法,认为子贡确实不如颜回。今人译作:“不如他啊;我同意你的看法,不如他啊!”[10]然而王阳明认为,孔子并非赞同子贡的回答,而是叹息子贡终究没有觉悟。言下之意,子贡只是专注于闻见上用功,远比不上颜回在心体上用功,这是王阳明解读此章的基本观点。
究竟要如何解读“女与回也孰愈”章?不妨先看原文。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
关于此章的解读,汉魏以来的学者并没有在“闻”这个观念上纠缠,这一章正如王弼所说,乃是“假数以明优劣之分,言己与颜渊十裁及二,明相去悬远也”[11]。朱熹则对“闻”的不同方式有所阐发:“一,数之始。十,数之终。二者,一之对也。颜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见终;子贡推测而知,因此而识彼。‘无所不悦,告往知来’,是其验矣。”[12]按照朱熹的注解,颜回的“明睿所照”与子贡的“推测而知”已经彰显出两人在认知方式上的差异。所谓“明睿所照,即始而见终”,即“如个明镜在此,物来毕照”,是指一种“彻头彻尾”的整体性认知,相当于悟解。而“推测而知,因此而识彼”乃是“如将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推寻”[13],是指一种经验性的推导,相当于知解。笔者认为,朱熹的这种解读很可能对王阳明产生了影响。
如果我们摆脱后世的注解,尤其是宋明以来的诠释,直接回到《论语》来看“女与回也孰愈”章,那么孔子对于颜回的赞叹未必不是从知识角度发出的感叹,即在获得知识所基于人的悟性以及逻辑分析能力等方面,孔子认为不仅子贡不及颜回,就是自己也有所不及。这原本是比较平实的理解。然而王阳明认为“闻一知二”的子贡是在闻见上(感官经验)用功,而“闻一知十”的颜回却是在心地(心体、本体)上用功,这种不同功夫的划分显然是为了论证他的“心即理”以及格物新说。其实孔子以六艺教授弟子,十分注重广博地学习这种方式,颜回也说夫子“博我以文”(《论语·子罕》)。因此,颜回的优秀并不是说他不在多闻多见上下功夫,只在内心上下功夫,他之所以超出同门,甚至连老师都自愧弗如,应当是他的悟性和反思能力(如《论语·为政》的“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专注而不懈怠(如《论语·子罕》的“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自强不息(如《论语·子罕》的“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以及勤奋好学(如《论语·先进》的“有颜回者好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之,“女与回也孰愈”章完全可以从知识与认知能力上进行诠释,而王阳明对子贡在闻见上用功的批判则堵塞了这条诠释进路。
二、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
王阳明与顾东桥的书信是探讨知识与良知关系的重要篇章。在来信中,除了以历史事件来质疑王阳明外,顾东桥着重以早期儒家经典中的“多闻多见”“好古敏求”“温故知新”等表述论证古圣先贤十分注重知识的探究,因而在闻见上做功夫不可或缺。王阳明则对《论语》中的这几章进行了重新解释,为自己的良知学说辩护。
首先,王阳明重新诠释了“多闻多见”与“多学而识”。
至于“多闻多见”,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而不能求诸其心,以阙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而所谓见闻者,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夫子尝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是犹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义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耳。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见闻之知为次,则所谓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窥圣门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使诚在于“多学而识”,则夫子胡乃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一以贯之”,非致其良知而何?(57—58)
王阳明认为“多闻多见”是孔子为了挽救子张的务外好高之病而发,并非积极教导子张为学的方式。这种理解是否有根据?我们不妨考察原文。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
无论是传统注疏还是现代人的理解,都认为此章就是孔子在教子张谨言慎行,这是从政的基本德行要求。如郑玄注曰:“言行如此,虽不得禄,得禄之道也。”[14]钱穆分析得更为清晰:“孔子不喜其门弟子汲汲于谋禄仕,其告子张,只在自己学问上求多闻多见,又能阙疑阙殆,再继之以慎言慎行,而达于寡过寡悔,如此而谋职求禄之道亦即在其中也。”[15]历史上关于此章的理解并无大分歧,“多闻阙疑”“多见阙殆”是孔子亲口所言,在多闻多见的基础上保持理性,在日常生活中谨言慎行,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主张,如何能得出孔子是在批评子张沉浸于多闻多见、好高骛远呢?王阳明为了论证孔子反对在多闻多见上做功夫,可以说是完全曲解此章。他甚至引用“不知而作”章中的“多闻多见”来加强论证,然而这一章能否证成他的观点呢?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
所谓“不知而作”乃是指那种穿凿妄作的现象,孔子自认为没有这种毛病。那么孔子采取何种方式避免这种毛病呢?那就是“多闻多见”,然后选择那些好的东西去遵从和记在心里。[16]可见“多闻多见”并不是一个否定性的说法,对所闻所见进行甄别和筛选,然后选择好的东西形成一种知识去奉行,这正是孔子一生都在做的事情。诚然,这种知识“是由学习而得,并非生而知之者。这样的‘知’,是仅次于‘生而知之’的”[17],故曰“知之次”。“知之次”源于《论语·季氏》中“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四个层次的划分。不过《季氏》篇中所讲的层次并不是指“知”本身的层次,而是指掌握“知”的人以及认知方式的层次[18],“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据。同理,本章中的“知之次”也应当理解为获得“知”的方式,孔子自认为属于“学而知之”的层次,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多闻多见正是一种“学”的方式。
至此可知,王阳明引用“不知而作”章并不能证明孔子反对“多闻多见”,更不能说明在多闻多见上用功不是孔门的修养工夫。相反,“子张干禄”章、“不知而作”章中的“多闻多见”正是人在经验世界中获得认知的一种方式,并且也是孔子本人一直在做的功夫。王阳明引用此章唯一能证明的是在孔子那里确实存在“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的层次划分,但正如上文所论,这种层次并不是“知”本身的层次,而是认知方式的层次。而王阳明显然是从“知”本身的性质角度进行划分,从而将“生而知之”归属为德性之知(亦即良知),“学而知之”归属为闻见之知(亦即经验知识)。德性之知乃是与生俱来的,并不是来源于经验世界。王阳明认为孔子无“不知而作”,这和孟子所讲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相通,显然“知”就是指人内心的良知。然而这种理解是否符合《论语》语境?孔子讲完“不知而作”后,紧接着讲“多闻多见”“择善而从”,显然这种“知”并不是指与生俱来的良知,而是指通过学习古代礼乐文化(“好古,敏以求之”“信而好古”皆可证)所获得的“知”(知识)。如果这种“知”真如王阳明所言是指良知,那么良知人人皆有,显然不存在“不知而作”的现象,除非将“不知而作”解读为“不遵循良知而创作”或“违背良知去创作”,然而这种解读显然有违原意。
王阳明对“多闻多见”的重新诠释,真正可能构成一种“挑战”的大概是《论语·卫灵公》中的“多学而识”这一章。从句面意思来看,孔子似乎否定了“多学而识”。然而孔子无论是教学生还是自己修养,都主张在多闻多见上做功夫,怎么会反对“多学而识”呢?很显然,孔子与子贡的这段对话有特定含义。孔门师徒对话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对话者的身份、学识、品性以及对话的情境等因素都会直接影响所论话题,如同样是“问仁”,孔子对颜回、冉雍、司马牛、子张、樊迟的回答各不相同。因此,孔子唯独对子贡说这番话是需要我们多去关注的,而子贡的身份、学识、品性等因素必然会促使我们重新理解孔子这段话的特定含义。在《论语》中,子贡算是出场比较多的弟子,那么子贡是一种什么形象呢?下面三段语录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尽管子贡与老师相处比较多,也极力维护老师、尊崇老师,但却未必是真正能理解老师的学生。当孔子发出“莫我知也夫”“予欲无言”这种感叹后,子贡不能真正地领会老师这番感叹背后的深意,不明白老师始终都有一种强烈的天命信念作为支撑。子贡十分关注老师的文章,正如他发现老师多闻多见、多学而识、好古敏求,然而这些都是日常经验中的功夫(现象),在这背后,孔子秉承着一种上达天道的信念,这正是“一贯之道”,而这些往往不能通过言谈、闻见来呈现,无怪乎子贡认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由此可见,孔子与子贡关于“多学而识”这段对话的真实意蕴并不是否认多学而识、多闻多见等日常下学工夫的价值,而是要激发子贡去体认下学工夫中的一贯之道。
在梳理了“多学而识”这一章的含义后,再回头看王阳明的解释,很显然,孔子并非否认通过“多学而识”“多闻多见”等日常经验功夫来获取知识的方式及其价值,只是因为子贡没能真正理解“下学上达”,不能一以贯之,因而孔子通过这种“遮诠”的方式来激发子贡,促使他对“道”的体认。如果子贡只是在多学多识、多闻多见上用功却丧失主体的自觉与信念,那就必然会陷入“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孟子·尽心上》)。当然,王阳明以“致良知”来诠释“一贯之道”,从儒学史的角度来看是具有合法性的。一以贯之的正是“道”,从具体内涵来看,既可以被曾子诠释为“忠恕”,也可以被阳明诠释为“致良知”,这正是儒家之道丰富性内涵的体现。
其次,王阳明重新解读了“好古敏求”。
“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58)
在“心即理”的基础上,将学习、探求全部解读为“心上学”“心上求”,这是十分典型的心学诠释。我们不妨看看《论语》原文: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生而知之”意味着先天而来的,而“好古敏求”则是指在经验世界中通过学习与探求获得的,那么这种“知”显然并不是指生来与俱的“良知”。“非生知之”与“敏而求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后一说法印证前文所讲的“生而知之”的“之”应当是指人伦社会关系中的道理(知识)。当时的人发现孔子知道很多关于社会治理、人伦道德、礼乐制度等方面的知识,深感惊讶,因而认为他属于那种“生而自有知识”的“上智圣人”[19]。但孔子明确反对这种评价,他曾言“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认为自己属于勤奋好学以获得知识的人。由此可见,孔子的“好古敏求”就是说喜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地去探求从而掌握、明白各种知识与道理。王阳明将“求”与“学”的内容全部解释为“心”(理),显然无法在《论语》中寻找到内证,并且这种解读掩盖了孔子对于经验知识学习的推重。
最后,王阳明重新解析了“温故知新”。
“温故知新”,朱子亦以“温故”属之“尊德性”矣。德性岂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于“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58)
“温故知新”最早出自《论语·为政》,又见于《中庸》。王阳明认为朱熹也将“温故”视为“尊德性”,显然是就《中庸集注》中“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20]而言的。存心也就是涵养德性,而德性显然不能求之于外。“知新必由于温故”意味着涵养德性、存养本心是根基,以“知”来主导新的实践活动乃是扩充德性的过程。尽管王阳明并没有从良知视角展开,而是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来论证“温故”与“知新”是一体的,但在阳明心学中,“温故”显然是就本体层面而言,“故”就是指存于内心的良知,“温故”就是要唤醒良知的自觉;“知新”就是要将良知扩充,产生新的道德实践活动,这一过程就是致良知。按照王阳明的逻辑,“温故知新”体现了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一致性。
然而,回到《论语》中,关于“温故知新”的理解,皇侃注曰:“故,谓所学已得之事也。所学已得者,则温之不使忘失,此是月无忘其所能也。新,谓即时所学新得者也,知新,谓日知其所亡也。”[21]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曰:“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22]黄式三认为:“故,古也,已然之迹也。新,今也,当时之事也。”[23]不论是将“故”训为“古”,还是解释为所学已得者、旧所闻,“故”都必然体现为关于过去的历史事件、道德文化、名物制度等方面的一些知识或道理。学习这些内容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要开出新义,产生新的理解或有新的体会,从而产生能在当下以及未来世界中发挥作用的知识与方法。其实孔子多次表明自己对于古代文化的兴趣与喜好,正是因为勤奋好学,他积累了很多关于古代历史文化、礼仪制度等方面的知识。“温故知新”既是孔子向学生传授的学习之道,更是他自己一直践行的学习方法。总之,王阳明将“温故知新”视为涵养德性之学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不能忽视其中所蕴含的知识向度。
三、良知之外别无知
在《答欧阳崇一》这封信中,王阳明着重解答了欧阳德关于良知与闻见之知关系的疑惑。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80)
这一段是王阳明关于“良知”(德性之知)与“知识”(见闻之知)关系的重要论述。首先,王阳明阐述良知与感官经验活动的关系:良知并不是在感官经验活动中产生的,这是讲良知的根源性(来源);但是人的感官经验活动都应当是良知流行和发挥作用的结果[24],这是讲“良知”的功能性(作用);所以良知并不会因人的有限感官经验活动而影响其自身的圆满自足[25],这是讲良知的超越性(本性);但是良知又不能脱离人的日常感官经验活动,这是讲良知的现实性(品格)。紧接着王阳明以《论语·子罕》中的“吾有知乎”章来加以论证。孔子自认为无知,这里的“无知”显然不是指没有良知,而是指没有知识。王阳明将“无知”诠释为“良知之外,别无知矣”[26],实在是一种惊人的解释![27]所谓“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意味着一切感官经验活动都必须在良知的主导下进行,一切知识都应当是良知的产物。如果人心时刻以致良知为事,那么一切感官经验活动(多闻多见)都是在做致良知的功夫;而日常感官经验活动都不过是良知流行作用的结果,这就再次解释了“良知不离于见闻”。最后,王阳明再次引用“不知而作”章中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来加强论证,既然讲“择”与“识”,那么“良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81),即主导这两种行为的必然是良知[28],可见良知不能缺席人的感官经验活动。王阳明特别提醒欧阳德“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这种讲法不妥,因为“求之见闻”这种表述是典型的程朱格物穷理的话语,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讲法容易将致良知与感官经验活动割裂开。
无独有偶,在《传习录》下卷中,还有一条语录也是探讨“吾有知乎”章。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来问,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两端,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增减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与之一剖决,便已竭尽无余了。若夫子与鄙夫言时,留得些子知识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体即有二了。”(128)
在王阳明看来,孔子并非先以“知识”去应对前来请教的鄙夫,他的内心只是“空空而已”,没有什么知识。孔子只是叩问鄙夫自身的“是非两端”,这个“是非两端”源自孟子的“是非之心”,是人与生俱来的,此即王阳明所谓的“本来天则”,即良知。这种“天则”不是源于经验世界(闻见),不是后天经验所得,因此即便是圣人也不能在任何人的良知上添附一分一毫。孔子所做的工作无非就是叩问鄙夫的良知,让其良知觉醒,进而充分拓展其良知,从而达到良知“竭尽无余”的状态。如果孔子一开始只是以“知识”去应对鄙夫,那么就无法竭尽他的良知,并且更为严重的是,“知识”脱离了“良知”,完整的“道体”支裂为“二”。可见,脱离良知的“知识”,往往会阻碍良知的呈现。
王阳明两次引用“吾有知乎”章来论证良知与知识的关系,可见此章的重要性。那么此章中“有知”“无知”该如何理解?王阳明的解读是否合理?先看此章原文。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
此章存在诸多解读难点,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少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有知”“无知”的理解。有的认为“有知”是指有私意,“无知”是指无意,如皇侃曰:“知,谓有私意于其间之知也。圣人体道为度,无有用意之知,故先问弟子曰‘吾有知乎哉’也。又,‘无知也’,明己不有知知之意也,即是无意也。”[29]“有知”“无知”是指有知识、无知识,如朱熹认为“孔子谦言己无知识”[30]。
第二,“空空如也”的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空空”是空虚、虚心的意思。但有人认为是指鄙夫的空空,如孔安国曰:“有鄙夫来问于我,其意空空然。”[31]邢昺疏曰:“空空,虚心也。”[32]有人认为是孔子空虚、无知,如黄式三曰:“空空如,自言心之虚也。”[33]焦竑认为是“孔子言己空空无所知”[34],潘重规认为“空空”是指孔子一无所知的样子。[35]黄怀信认为是孔子自谓空虚,自嘲无知。[36]第二种观点认为空空即“悾悾”,诚恳的样子。如梁章钜认为“空空”即“悾悾而不信”之“悾悾”,包咸注:“空空,悫也。”[37]“悫”即诚实貌。杨逢彬亦持这种观点。[38]
第三,“竭”的理解。孔子竭尽其所知,如孔安国认为:“我则发事之终始两端以语之,竭尽所知,不为有爱也。”[39]朱熹认为:“孔子谦言己无知识,但其告人,虽于至愚,不敢不尽耳。”[40]竭尽其诚,如邢昺认为:“此章言孔子教人必尽其诚。”[41]
笔者认为,此章的“有知”“无知”分别指“有知识”“没有知识”,孔子虽然勤奋好学,多闻多见,但并非无所不知,“吾有知乎哉”与其说是孔子谦虚,不如说是坦诚,孔子确实有很多东西不知。比如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和蔬菜[42],孔子自认为“不如老农”“不如老圃”(《论语·子路》),很显然,孔子并不是谦虚,他在这方面所掌握的知识确实比不上田农和菜农。虽然“吾有知乎”章中的“鄙夫”向孔子请教的具体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所问和樊迟一类的问题,那么孔子恐怕是很难回答的。此章前两句中的“有知”“无知”是确定此章的主题,后面“鄙夫求教”的故事则是论证孔子之“无知”。“空空”与“竭”都是用来证明孔子之“无知”。“空空如也”如果理解为鄙夫的态度诚恳或内心空虚,那就与题旨相距甚远了,所以将“空空如也”理解为孔子对于鄙夫的提问心里完全没有底、一无所知的样子,更为合理。但是别人来请教你,总不能像对待学生樊迟那样两句话就随意打发,而孔子能做的就是通过“叩其两端”的方式来应对,做到这一点,孔子也已经竭尽自己的所知与所能了。
综上所析,“吾有知乎”章完全可以从知识角度进行阐述,这与孔子强调学习、注重在多闻多见上做功夫的思想是一致的,而王阳明的诠释很显然忽视了孔子思想中注重知识的向度,将“无知”诠释为“良知之外,别无知矣”,完全将此章作一道德哲学的诠释,可以说是超出了原文语境。
四、知识无关乎成圣
顾东桥在写给王阳明的书信中,坚持为程朱理学的格物穷理学说辩护,既引历史事件相质疑,又引《论语集注》中“生而知之”章尹焞的注解来证明。
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59)
顾东桥认为,“生而知之”的是义理,而“学而知之”的乃是经验性的知识,后者必然要通过格物穷理的方式来获得。王阳明则从格物穷理所要成就的圣人人格这一最终目标入手,他说:
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60)
格物穷理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修养功夫,这种功夫最终是要成就圣人人格,这一点在宋明理学家那里无疑是一种共识。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追问,究竟什么是圣人?王阳明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31)他还有“心之良知是谓圣”(312)、“心之良知谓之圣”[43]的讲法。简言之,圣人的标准就是良知,能够彻底致良知,使得人心达到纯粹天理的状态,那就是圣人。至于具体知识、才能等,都与成圣无关。“学”也不是学礼乐名物之类的知识,而是学“义理”,学习这种活动本质上就是致良知。既然知识无关乎成圣,那就不必以知识去苛求圣人。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指出:
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如“子入太庙,每事问”之类,先儒谓“虽知亦问,敬谨之至”。此说不可通。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110)
只有“天理”才是判断圣人的唯一标准,圣人“无所不知”“生而知之”都是在讲天理,亦即良知。良知就是本体,是一切经验活动的根据与原则。良知虽然澄明了,但并不能因此推论圣人就知晓经验世界中的一切具体名物制度、草木鸟兽等,因为这些都属于知识。所谓“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意味着那些无益于德性涵养的知识,圣人的良知自然不会去探求;所谓“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意味着那些应当知道的知识,圣人自然能在良知的指导下去获得。为了论证这一点,王阳明批驳了程颐对“子入太庙,每事问”的诠释。“虽知亦问”的讲法背后显然是圣人无所不知的思想,而王阳明区分“良知”与“知识”,只将“良知”置入“圣人”的内涵之中,这就彻底解决了圣人“生而知之”的问题。[44]简言之,知识无关乎成圣。尽管王阳明对“子入太庙”章的解读肯定了礼乐名物类“知识”的客观存在,但主张“知识”必然要被良知所统摄,即“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然而知识如何能统摄于良知之下?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非本文所能详论。[45]
五、经典诠释的边界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王阳明在确立“心即理”的核心观念后,批判了朱熹所倡导的即物穷理而知致的进路,重新诠释了《大学》的“格物致知”,进而对《论语》中的“多学而知”“多闻多见”“有知无知”等表述进行了重新解读。王阳明认为在多闻多见上做功夫不如在心体上做功夫,向外学习与探究所获得的知识并不是道德行为的根据与原则,人心内在的良知才是一切经验性活动的终极根据。从心学自身的体系来看,这些论证确立了良知的本体地位,将德性涵养视为一切现实经验活动的根基,对于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无疑具有重要价值。然而,王阳明以“良知”“天理”为核心来诠释《论语》中的“知”与“学”,将“无知”诠释为“良知之外,别无知矣”,主张“致知之外,更无学”(243),对于孔子积极倡导的“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多闻多见,择善而从”等均予以消解,显然背离了《论语》的语境,遮蔽了孔子对于学习知识的推重。
王阳明对《论语》的诠释足以引发我们思考:经典诠释是否有边界?经典诠释是否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要探讨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经典诠释的类型或方式。毕竟在中国哲学史上曾存在着汉学与宋学两大诠释流派,它们分别对早期儒家经典进行诠释,但又彰显出不同的诠释特征。一般认为,就这两个诠释流派的经典诠释方法而言,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汉学运用小学的方法,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等,对经典中的字词句、名物等进行考证,追求经典原始含义的还原,体现出一种客观精神。宋学则注重对儒家经典的精神主旨、天道人道的发掘,探究微言大义,为现实生命体的生存在世提供某种根据与原则,这是一个追求生存意义与生命价值的诠释进路,体现出人的主体性精神。当然,这两个诠释流派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汉学中存在着重训诂与重微言大义并存的情形,其重视微言大义,也就是一定程度上重义理;宋学除以重义理为特征外,亦有重训诂考辨的”[46]。那么这两个传统的诠释流派是否有各自的边界呢?换言之,诠释者在进行经典诠释的时候,不管是偏重训诂还是偏重义理,是否要遵循某种客观的规则?笔者在这里想引用景海峰教授和黄俊杰教授的研究来略加讨论。
景海峰教授指出,传统的解经学以经典文本的解释为中心,解释的目的就是使文本的内容清晰化,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经典所传递的意义,因而着重处理语言文字所带来的问题,同时需要划界,以便排除各种对意义确定性可能产生的干扰。由此,经典的解释活动就形成了一定的界域和自身的封闭性。这意味着传统解经学所主导的诠释活动是有边界的。但是景教授指出,在经学体系走向瓦解之后,这种传统的解经学已经难以为继了,解经学需要走向现代的诠释学。那么现代诠释学会不会导致完全忽视或违背经典原初的含义?当然这里还有更深层的问题,即经典是否存在原初含义。景教授沿用了利科《记忆,历史,遗忘》中对历史的两种划分,一是作为事件(事实)的整体,一是和事件有关的话语之整体,即历史学家对于过去的见证、叙事、解释和表象。前者是连续体,没有开始;而后者属于创造的历史,从生存论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给定它一种始源性。因此,作为历史创造和叙述的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话语系统,具有始源性和本真性。但他同时指出,经典的本真性也是一个被塑造的过程,我们不能想象回到一个静止的原点,而只能在“原初性”这个观念的理解上来构成各种各样的叙述范式。[47]其实,就本真性而言,笔者认为应该区分“经典的本真性是否存在”以及“经典的本真性能否被认知”,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经典文本作为一种表达或叙述,最初叙述者想要表达的含义是确切的,是真实而又客观存在的,这就是经典文本的本真性、原初性。比如《论语》中“樊迟问稼”这一章,孔子的回答显然蕴含着他的真实想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定能准确地把握这个原初含义,尽管我们仍然在使用相同的文字,但字词的读音、语义都在改变,故事中人的身份、对话的语境等信息我们掌握不完整。因此,要完全理解经典文本的真实含义,可以说困难重重。但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客观困难,才使得对本真性的追寻有意义,诠释因此成为必要,对文本的不断诠释活动恰恰是文本成为经典的过程,也是经典焕发新意的过程。那么在经典的诠释过程中,诠释者是否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
黄俊杰教授认为,思想命题一经原创者提出之后,就取得自主性,原创者无法拥有思想命题的所有权。更进一步看,虽然原创者并不能独霸思想命题的所有权,但是异代异域的解释者,在从事经典解释时也不能拥有绝对的“自由”,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浸润在自己的时代思想氛围之中,而且他们更必须通过孔孟、朱子以及他们各自国家前辈的“诠释的权威”来印证,也在“述”与“作”之间求其平衡。[48]黄教授主要是就东亚儒家经典的诠释史而言,这是一种对诠释规律的概括。以史为鉴,那是不是可以说,即便走出了传统的解经学,如果我们在今天要建构一种新的经典诠释学,也仍然要遵循一定的规范或原则?
笔者认为,经典诠释是有边界的,当然这里的“边界”不是说诠释活动本身的有限性,而是指经典诠释应当遵守客观的原则。笔者将这种原则大致归纳为三个:一是语言学原则。这里的语言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语义学、语法学、语源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等。经典文本由以构成的字词句、篇章结构等都是客观的,因此经典诠释必然要遵循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等客观规律,这应当成为经典诠释的首要原则[49]。二是历史情境原则。经典文本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经典中的人、物、事都有着特定的历史痕迹,很多观念是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忽视历史情境,往往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与理解[50],或枉费心力去为之辩护[51]。三是逻辑自洽原则。经典诠释必然要对经典进行全面的理解,而不是断章取义,因此诠释所使用的概念应当贯通经典本身,形成逻辑自洽。宋明新儒学作为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从整体上来说是成功的,因为理学家们将“天理”等范畴融贯于早期儒家经典,并建构了思想体系。
回过头来再看王阳明对《论语》的诠释。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本源于孟子,但这是否意味着以“良知”来诠释《论语》中的“知”就是合理的呢?知识与良知的关系原本不是早期儒家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区分最早源于张载与程颐,然而朱熹似乎并不认为两者截然不同,正如余英时指出的,朱熹力图使儒家之“道”智识化,并且由于他的巨大影响,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之间的差别几乎完全被人遗忘,直到王阳明的出现。[52]德性之知(良知)与闻见之知(知识)的关系是阳明心学中的重要问题,很早就引起学界的关注。熊十力曾主张致知宗阳明,格物本朱子,尝试圆融地协调两者关系。后来牟宗三提出良知坎陷自己从而转化出了别心以成就知识系统,最终将知识统摄于良知之下。唐君毅则明确分析良知与知识的四种复杂关系,以证两者之不可分离。[53]近来,杨泽波教授指出,王阳明自认为接续孟子之学,殊不知“孟子虽然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性,但也不自觉地丢掉了孔子的智性”,而王阳明却“并没有意识到孟子与孔子思想的差异”[54]。如果这个结论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就不难理解王阳明对《论语》的这种诠释了,而这显然客观上造成了对孔子思想中注重知识这一面相的忽视。今天我们重新审视王阳明对《论语》的诠释,更能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得失,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中国哲学的经典诠释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本文初稿曾分别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办的“儒家的人文主义、意义世界及实践智慧——中华孔子学会2023年会暨纪念张栻诞辰890周年学术研讨会”以及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举办的“儒家古典学与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经典诠释与语文学方法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承蒙学界师友指正,特致谢意。
[1] 按照王阳明自己的说法,他曾经注解过《大学》《中庸》,据《与陆原静(丙子)》记载:“所问《大学》《中庸》注,向尝略具草稿,自以所养未纯,未免务外欲速之病,寻已焚毁。”(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四,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86页。本文所引王阳明诗文均据此版本,下文仅标注页码)
[2] 钱德洪在《大学问》后附的跋引王阳明的信曰:“《大学或问》数条,非不顾共学之士尽闻斯义,顾恐借寇兵而赍盗粮,是以未欲轻出。”(1072)
[3] 刘笑敢指出,王阳明的《传习录》《大学问》都是关于经典的解说和辨析,虽无形式之完整,却有内容之精深;虽无严格的注经的形式,但并非没有注经、说经之实。参见刘笑敢:《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
[4] 学界很早就关注到王阳明对《论语》的诠释,如马忠杰、张宏敏:《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句的一种解读——以王阳明〈传习录〉为中心的考察》,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5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孙宝山:《王阳明的〈论语〉诠释》,《孔子研究》2014年第1期;王玉彬:《阳明心学视域下的〈论语〉诠释——以朱熹〈论语集注〉为参照》,王钧林主编:《海岱学刊》(2015年第1辑),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郭亮:《王阳明释经学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牛冠恒:《圣学·心学·实学的统一:王阳明〈论语〉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乐爱国:《王阳明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及其后学的变异——兼与朱熹的解读比较》,《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毕景媛:《王阳明〈论语〉诠释的心学立场及本体意蕴》,《东岳论丛》2022年第3期;唐明贵:《王阳明〈论语〉诠释的“浙学”特色》,项楚、舒大刚主编:《中华经典研究》(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另外日本和中国港台地区也有一些研究,详见孙宝山所列。
[5] 语录分条编号依据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传习录》中卷乃是书信,故同一封信中重复引用《论语》中相同的内容,只计一条。
[6] “入太庙,每事问”两句在《论语》中重出,分别见于《八佾》和《乡党》,王阳明主要是针对朱熹《论语集注·八佾》中的注释而言,可见《传习录》只未引用《论语·乡党》一篇。
[7] 《传习录》上卷徐爱所录主要发生在正德七年(1512),当时徐爱以祁州知州考满进京,陪侍阳明半年左右。详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673、686页。
[8] 黄绾认为:“甲戌,升南京鸿胪寺卿,始专以良知之旨训学者。”(1559)甲戌年即正德九年(1514),王阳明43岁时已经倡导良知学说,这个说法应当比较可靠。
[9] 朱熹:《论语集注》卷三,《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7页。
[10] 孙钦善:《论语本解》(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53页。关于此章“吾与女弗如也”的理解,错综复杂,历史上有的《论语》版本可能作“吾与汝俱不如也”(《论衡·问孔》),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曰:“既然子贡不如,复云吾与女俱不如者,盖欲以慰子贡也。”《后汉书》李贤注引《论语》云:“吾与女俱不如也。”甚至还有作“吾与女皆不如也”(详见黄晖:《论衡校释》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03页)。如此一来,凡有“俱”“皆”字则“与”当作连词,意即孔子认为自己与子贡都比不上颜回。然传世《论语》版本皆无“俱”字,故关于“与”字之理解今人分成了两派。一是作连词,意即“和”,如程树德《论语集释》、钱穆《论语新解》、蒋绍愚《论语研读》、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等;一是作动词,意即“赞同”,如朱熹《论语集注》、潘重规《论语今注》、杨伯峻《论语译注》、孙钦善《论语本解》等。
[11] 皇侃:《论语义疏》卷三,高尚榘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06页。
[12] 朱熹:《论语集注》卷三,《四书章句集注》,第77页。
[13]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八,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21页。
[14] 皇侃:《论语义疏》卷一,高尚榘校点,第38页。
[15] 钱穆:《论语新解》,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39页。
[16] “多见而识之”一句应当视为“多见,择其善者而识之”的省略,这大概可以看作是俞樾所讲的“古人行文不嫌疏略”的一个例证。
[17] 潘重规:《论语今注》,台北:里仁书局,2000年,第146页。
[18] 孙钦善认为,孔子按智力、知识把人分为四等,前两等属于人性的差别,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者”,无疑是先天的天才论观点。后两等则属于学习态度的差别。可见孔子关于才智分等的思想,既包括先天的因素,又包含后天的因素。参见孙钦善:《论语本解》(修订版),第235页。
[19] 皇侃:《论语义疏》卷八,高尚榘校点,第433页。
[20] 朱熹:《中庸集注》,《四书章句集注》,第36页。
[21] 皇侃:《论语义疏》卷一,高尚榘校点,第33页。
[22] 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四书章句集注》,第57页。
[23] 黄式三:《论语后案》,黄式三、黄以周:《黄式三黄以周合集》(第2册),詹亚园、张涅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1页。
[24] “见闻莫非良知之用”的字面理解是,所有的感官经验知识无不是良知的作用。但这种理解并不能真正地彰显王阳明的本意。因为一方面经验世界中确实存在着独立于良知的知识(详见下文“知识无关乎成圣”节的分析);另一方面,现实中人的感官经验活动并非全都在良知的主导下展开,否则就不存在违背良知的情形了。因此,这句话应该理解为:人的感官经验知识都应当是良知发挥作用的结果。
[25] 陈来认为,“不滞不离”是佛教常用的表述模式,“良知不滞于见闻”指良知不受见闻的局限,这是指良知本身。而“亦不离于见闻”是指致良知。参见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1页。
[26] 王阳明在《与马子莘(丁亥)》的书信中亦曰:“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243)
[27] 杨泽波教授指出,“良知之外,别无知”“良知之外,更无知”,实是惊人之语。这种说法可作两种解释:一是良知是唯一的道德根据,是唯一的“知”,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的“知”;二是良知已包含“智性”之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知”。参见杨泽波:《论阳明心学存在的偏颇》,《哲学研究》2022年第3期。
[28] 这就是牟宗三所讲的,知识行为既是一行为,则致良知之教义仍可用其上,即“知识行为”亦是良知天心所自决。参见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1页。
[29] 皇侃:《论语义疏》卷五,高尚榘校点,第214页。
[30] 朱熹:《论语集注》卷五,《四书章句集注》,第111页。
[31] 皇侃:《论语义疏》卷五,高尚榘校点,第215页。
[32]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朱汉民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8页。
[33] 黄式三:《论语后案》,黄式三、黄以周:《黄式三黄以周合集》(第2册),詹亚园、张涅主编,第304页。
[34] 焦竑:《焦氏笔乘》,李剑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73页。
[35] 参见潘重规:《论语今注》,第179页。
[36] 参见黄怀信主撰:《论语汇校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74页。
[37]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七,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85页。
[38] 参见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0页。
[39]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七,程俊英、蒋见元点校,第586页。
[40] 朱熹:《论语集注》卷五,《四书章句集注》,第111页。
[41]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朱汉民整理,第128页。
[42] 关于樊迟学稼的历代诠释,可以参见黄俊棚:《“樊迟学稼”诠释史》,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
[43] 王阳明:《稽山承语》,转引自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28页。
[44] 按照王阳明的讲法,不仅圣人生而知之,“众人亦是‘生知’”(108),“人胸中各有个圣人”(105)。
[45] 学界对此早有关注,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学者都有探讨,详见赵卫东:《分判与融通——当代新儒家德性与知识关系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
[46] 蔡方鹿:《论汉学、宋学经典诠释之不同》,《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
[47] 参见景海峰:《从解经学走向诠释学——儒家经学现代转化的哲学诠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48] 参见黄俊杰:《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中的三个理论问题》,《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49] 诚然,要真正建立起这种原则确实不易,毕竟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以《孟子·告子上》中的“乃若其情”之“情”的训释为例,至今仍然存在着分歧,有的解为情感,与“性”相对,如赵岐、朱熹、焦循、李景林等;有的解为实、实情,如戴震、徐洪兴、杨泽波等;有的解为资质、材质,如陈蒲清、杨逢彬等。但我们不能因为存在诸多争议,而忽视特定历史时期的语言、文字、语法等方面的客观规律。
[50] 这种历史情境包括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礼仪习俗等方面。比如《论语》中的“君子”“小人”这两个观念并不都是从道德上来讲的。杨伯峻、赵纪彬等人都有相关探讨,杨逢彬又有一些补充论证。详见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第27—32页。
[51] 学界曾经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等做过不少辩护,不少人甚至自认为是在做正本清源的工作,其实很多诠释不过是为了捍卫诠释者心中的某种信念或价值观而已。
[52] 参见余英时:《朱熹哲学体系中的道德与知识》,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杨立华、吴艳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72页。
[53] 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19—323页。
[54] 杨泽波:《论阳明心学存在的偏颇》,《哲学研究》2022年第3期。
- 编辑: 张益豪
- 统筹: 侯绍华 李沅栗
- 编审: 翟 佳 周之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