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石窗 | 闽学源头在同安的“体相用”三佐证——朱熹主簿四年的学派建树考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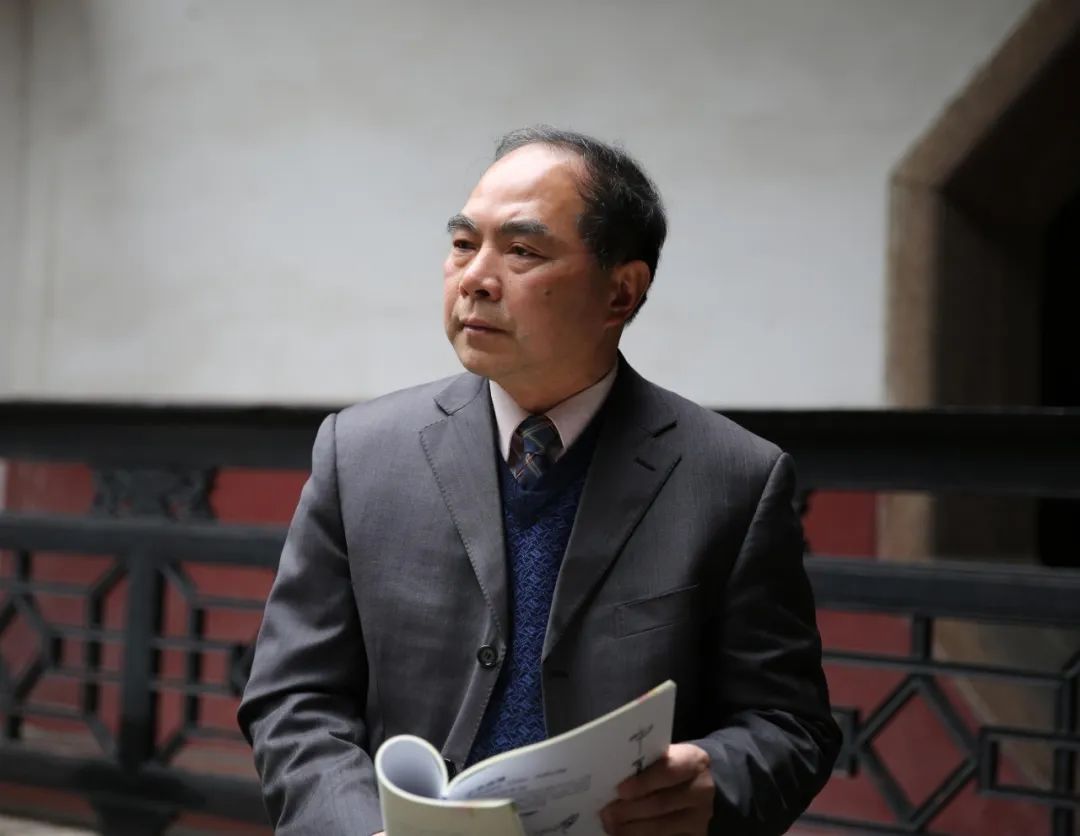
本文来源:《孔学堂》(中英文)2024年第4期。
摘要:由朱熹所奠基的理学,因其诞生于福建,又称作“闽学”。朱熹在同安主簿任上已经形成了其基本的思想文化主张,这种主张通过门人以及后来的追随者不断传承与发展,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宏大影响的学派。从思想上看,闽学是一个内容丰富并且具有宽广包容性的思想文化整体,它以弘扬儒学为核心,兼容了释道思想以及民俗文化等诸多因素,以生命道德的自我完善为求学之切要,以社会安康为治世的基本目标,立足经学传承与道德实践的统一,重视纠偏除弊、移风易俗、开拓进取。朱熹于同安任职尽管只有四年时间,但他把教育事业做得有声有色,而他的助手与他培育出来的一大批门徒也都尽心尽力,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文化建树。
关键词:闽学源头 朱熹 同安 体相用
作者詹石窗,四川大学杰出教授。
一、引言
作为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朱熹在海内外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关学术研讨会不断召开,关于朱熹研究的学术论著与日俱增,人们关注朱熹文化贡献的热度持续升温,这反映了社会对于汲取传统文化精华的迫切要求。
朱熹一生勤于著述,可谓著作等身。由于热心教育,朱熹的门人甚多,从而逐渐形成了朱子学派。自南宋中期至今,朱子学传承不绝。历史上,人们习惯于从发生地上来命名学术流派,因为朱子学诞生于福建,所以又称作“闽学”。
众所周知,学术研究,素有从源及流的法度,故而,闽学源头的追溯,就成为整体闽学研究的一大关键。在这个问题上,颜立水先生在《朱熹在同安》这部专著里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在多次研讨会上讲述朱熹于主簿任上的教育文化建树,为深入考察闽学源头打开了一扇大门。另外,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上,高令印先生提交的《朱熹在闽南与“闽学开宗”》一文指出闽南为闽学开宗之地,具体而言就是开宗于朱熹任泉州府同安县主簿期间。读了两位前辈的论著,笔者深受启发。这段时间,笔者重新阅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等历史文献,对于闽学开宗问题有些粗浅的见解,现不揣浅陋,整理成此小文,以就教于方家。
为什么说闽学开宗在同安呢?首先,朱熹在同安主簿任上已经形成了基本的思想文化主张,他的主张通过门人以及后来的追随者不断传承与发展,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宏大影响的学派;其次,闽学是一个内容丰富并且具有宽广包容性的思想文化整体,它以弘扬儒学为核心,兼容了释道思想以及民俗文化等诸多因素,以生命道德的自我完善为求学之切要,以社会安康为治世的基本目标,立足经学传承与道德实践的统一,重视纠偏除弊、移风易俗、开拓进取,这种特质在朱熹首任同安主簿时期的学术教育过程中即已奠定了基础,而后逐渐完善。
在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史上,有“体相用”的重要概念,这三个概念初起于佛学,而后逐渐为文化学者们所接受。一般地说,所谓“体”指的是万法之本体,即事物的主体及其本质特征;“相”指的是事物的表象,包括物理现象、生理现象、心理现象;“用”指的是万物诸法的作用。将“体相用”三者结合起来分析问题,有助于把握事物的整体状态。沿袭我国传统文化哲学的思路,笔者借助“体相用”的概念来阐述闽学源头在同安的问题,希望能够对该问题的探讨有所推进。
二、观物赋诗,借相以寄志
以往考察闽学源流的学者,大多会从经典义理、思想主张的诠释入手,这固然很重要;不过,如果翻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还会发现其诗赋作品占有相当分量,这也是闽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值得重视。
事实上,自孔夫子以“六艺”授予生徒时,就将“诗教”列于先。所谓《诗》《书》《礼》《乐》《易》《春秋》的顺序,从侧面反映了儒家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诗歌学习与素质培育。所以,自汉代以来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的文集,大多汇聚了诗词曲赋等文学作品。朱熹秉承先儒,也雅好写诗作赋。他的主簿四年生涯,几乎走遍了同安的山山水水,既留下了大量的题刻,也即兴感怀,写下别具一格的诗歌。古人云:“诗言志,歌永言。”朱熹写诗,当然不是什么无病呻吟,更不是装潢门面,而是有感而发。他善于借助特定环境,捕捉文学意象,以寄托他的思想情操,由此而造就了闽学特有的内涵丰富的“相”,闽学源头的考察当然不能忽略这些作品。
颜立水先生曾经写过《朱熹在同安的“纪游诗”》,择取朱熹留下的部分诗歌作品进行赏析,颇得其情趣。读了颜立水先生这篇文章,笔者继续追踪,发现那首脍炙人口的《观书有感》特别值得注意。诗云: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
这首诗到底什么时候写的,作于何处?向来有不同看法。有人以为“半亩方塘”是在尤溪的南溪书院文公祠前,认为那是朱熹幼年读书、游戏之所,因此推断此诗当作于尤溪。然而,朱熹离开尤溪时仅有五岁,而此处的“半亩方塘”是明弘治十一年(1498)方溥浚所修,客观时空否决了朱熹作诗于尤溪文公祠前的可能性。此外,尚有人指出此诗当出于建阳考亭的“半亩方塘”,以为朱熹于南宋绍熙二年(1191)四月从漳州离任后,就直接到建阳县城,在考亭新居大门外凿建半亩方塘,并在其上建“天光云影亭”,但其依据的史料是嘉靖《建阳县志》,而其“有意为之”的做法显然不符合朱熹赋诗的情境。
检索《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的《观书有感》其二云: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2]
在审美情趣方面,朱熹不喜欢刻意的人工造作。他所欣赏的是“自在”,因此其原初意象一定是自然景观。所以,视此《观书有感》出于建阳考亭也没有充足理由。至于莆田黄石城山国清塘、浙江淳安、新昌等处的“半亩方塘”,虽然都有相互对应的景观,但都是朱熹诗作之后的仿照物,找不到原始的文献实证。
其实,最早收录《观书有感》诗作乃是《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而该书卷三十九《答许顺之》也引述了《观书有感》第一首。其答书行文如下:
此间穷陋,夏秋间伯崇来相聚。得数十日讲论,稍有所契,自其去,此间几绝讲矣。幸秋来老人粗健,心间无事,得一意体验,比之旧日,渐觉明快,方有下工夫处。日前真是一目引众盲耳。其说在石丈书中,更不缕缕,试取观之为如何,却一语也。更有一绝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试举似石丈。如何湖南之行,劝止者多。然其说不一,独吾友之言为当然,亦有未尽处。后来刘帅遣到人时,已热遂辍行。要之,亦是不索性也。[3]
这封回信的对象许顺之,系朱熹于同安任主簿时的学生。据广平府知府李清馥所撰《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八所载:朱熹门徒有许升者,“字顺之,别号存斋,同安人,生长华宗,视纷华势利,无足动心,独有志圣贤之道。朱子簿同安,公年十三,即从讲学淬励。五年,秩满,复从北归,覃思研精,学力大究。朱子称其学专,用心于内,尝书“存斋”二大字授之,使扁书院,复为之记,临别宿云际寺”[4]。按李清馥的记载,临别之际,朱熹还特别写诗给许顺之作为纪念,由此可见朱熹对这位同安门人是相当器重的。朱熹离开同安之后,又两次写信告知如何“养气”与“修齐”的办法。
朱熹给许顺之的复信言及“湖南之行”,可以肯定是在离开同安多年之后。按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的记载,此答书是在乾道二年(1166),即湖南之行前一年,时年朱熹37岁,于同安离任(1158)已有8年。初看起来,似乎与同安无关,但若仔细推敲,却感觉原来朱熹是在回忆往昔的情况。
文物普查发现,同安莲花军营村“漆仙尾”山上有“半亩方塘”石刻。根据这一线索,笔者于2023年2月9日上山考察。当日细雨绵绵,云雾缭绕,但方塘仍清晰可见。大抵为半亩空间,至今泉水汩汩流出,清澈见底,两侧山丘耸立,颇有一鉴照影、别开生面的感觉。离方塘不远处的山腰间,见一巨石,松柏掩遮,长约二丈许,高约一丈许,其上方平坦有题刻,字迹虽已风化难辨,且有尘土填塞,但稍加清理,仍可看出“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诸字,因一段泥尘填塞较多,一时难于看全,但“窥一斑可知全豹”,故笔者判断此题诗当为朱熹《观书有感》其一的原初样貌。军营村主任高泉伟先生说:听老辈人讲,方塘附近有小屋,迄今地基犹存,乃先士人于此读书所在。笔者蠡测:朱熹当年对整个同安县“走透透”,连最南端的金门都去了,而军营离县衙并不算太远,且有官道通行至界临的安溪县,故而此地的“半亩方塘”极有可能成为朱熹作诗的原初意象。
朱熹之咏“半亩方塘”,表面看来是写景,但其实是借助景观而寄托读经的感悟,背后蕴含深刻的理学精神。关于这首诗的思想内涵,前人有不少解读。宋代罗大经于《鹤林玉露》中指出:朱子此诗“盖借物以明道也”[5]。又见宋代熊节编《性理群书句解》概括其理趣:“此篇形容本体清明之象。”又句解之:“半亩方塘如一镜之开,所以状吾心之体也”;“天光云影皆徘徊其间,所以言万理之涵具也”;“问他安得清明如此,所以喻吾心之静定昭明也”;“盖由源头常有活水来耳。程子有云‘涵养须用敬’,人之一心,能敬以养之,则天理流行亦犹是也”[6]。从这些解说不难看出,朱熹的咏物写景诗实在是其理学思想的隐喻,由“相”而悟“理”,可谓意味深远。如果不将此类诗作纳入其理学思想体系的考察范围,将是一大缺陷。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录的诗歌中,有许多包含了同安的地名,例如《游梵天寺》《梵天观雨》《同僚小集梵天寺坐间雨作已复开霁步至东桥玩月赋诗二首》《与诸同寮谒奠北山过白岩小憩》《同安官舍夜作二首》《再至同安假民舍以居示诸生》。此外,尚有几首是朱熹出游同安附近区域所留诗,例如《南安道中》《安溪道中》《安溪书事》《小盈道中》《题九日山石佛院乱峰轩二首》。这些诗歌反映了朱熹于同安主簿期间的公务活动以及生活起居情况,其中有四首关涉佛教,有一首关涉道教。由此可见,作为儒学传承人的朱熹并非对佛、道教漠不关心,而是怀有浓厚兴趣,这是研究闽学源头乃至整个闽学思想体系所应该注意的。
以往一些研究朱熹的学者总喜欢说他“逃禅归儒”,好像朱熹见了李侗之后就彻底屏去佛学思想,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至于他对道学的关注,从其《与诸同寮谒奠北山过白岩小憩》可略见一斑。所谓北山就是北辰山。考《论语·为政》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以北辰为象征,表达道德教化的意义。后来,制度道教以北极表征玄天上帝,隐喻生命涵养应该遵循天道的理念。历史上,闽王王审知以北辰山作为祭奠天神的坛场。朱熹与同僚谒奠北山,看起来是依照传统礼仪举行祭奠的,这符合同安本有的民俗,也有中华传统礼仪的文化依据,我们研究闽学源头没有必要回避这种历史;相反,实事求是地论述这个问题,才能全面客观地把握闽学源头的方向。
三、振兴县学,切用以育才
如果说朱熹于同安主簿任职期间撰写的系列诗歌,作为一种“相”而寄托了自己的生命修养与儒释道三家文化融通的思想趋向,那么他振兴县学的种种措施,则是从教育入手来建构新的人才培育模式,体现了闽学源头的切用特点。
朱熹于同安任职主簿,但他似乎对县学教育更为关心,故而投入的精力相当多。初到同安的时候,他就发现当时的县学有许多不对劲之处,例如书斋的结构布局与名称,都存在问题,故而需要整顿。其所撰《更同安县学四斋名》称:
学旧有四斋,许同年去其半,以省长谕具员之冗。故今唯两斋而四门如故,又皆错乱不得其所。至于命名之义,亦有未安。盖如汇征之名,乃学优而仕之事,非学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禄诱人,岂敩学者之意哉?今欲复四斋之旧,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目之,东西相次,自北而南,诵习之区,各仍旧贯。易日新长谕为志道长谕,汇征长谕为游艺长谕,其据德、依仁两斋请学谕、直学选本位学生(不系教养人——引者注:原系小字),权充斋长或斋谕,许随众升堂听讲,本学更不差人,以塞希觊之路,诸职事以为如何?幸与诸生议,以见告,条其便不便者。熹且罢行之。[7]
从这段描述可知:县学教室本有四屋、四门;后来精简,只剩下两屋、四门。在朱熹看来,最大的问题在于名称。原有名称基于“学而优则仕”的功利目的,虽然符合一般举子的追求,但并不是应该优先考虑的,说到底是以利禄诱人,背离了育人之本。因此,朱熹提出变更思路,恢复四屋、四门的格局,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名,这实际上是从根本上确立县学教育的思想纲领。《论语·述而》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三国经学家何晏解释说:“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矣也。据,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据也。依,倚也,仁者功施于人,故可倚之也。艺,六艺也,不足据依,故曰游也。”[8]对照一下《论语》原文及其何晏的注解,可知朱熹为县学更名,乃是从品学兼优的价值取向上考虑的,旨在屏去急功近利的偏差,杜绝妄想。而名称与方位的对应也有深意,所谓“东西相次,自北而南”讲究的是自然秩序,其中的“东西相次”蕴含的是“龙东虎西”,龙虎护卫,阳阴呼应;而“自北而南”最为切要,从五行上看,“北”为“水”之位,为阴为柔,气由下生,左旋右转,由水而生木,由木生火,由火生土,由土生金,形成了五行相生、和合有常的天道秩序。所谓“新”指的是天地日新,而“长”指的是生生不息,日新而能长,因长而日新,激励学子守正创新。
在更新县学门名的同时,朱熹注重树立典范。为此,他主导了苏颂祠的建设。其所撰《苏丞相祠记》称:
熹少从先生长者游,闻其道故相苏公之为人,以为博洽古今,通知典故,伟然君子长者也。
熙宁中掌外制,时王丞相(引者注:王安石)用事,尝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罢归。不自悔,守益坚,当世高其节,与李才元、宋次道并称三舍人云。后得毗陵邹公所撰公《行状》,又知公始终大节,盖章章如是。以是,心每慕其为人。属来为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为问县人,虽其族家子不能言,而泉人往往反喜道曾宣靖、蔡新州、吕太尉事以为盛。予不能识其何说也。然尝伏思之,士患不学耳。而世之学者,或有所怵于外,则眩而失其守。如公学至矣,又能守之,终其身一不变,此士君子之所难,而学者所宜师也。
因为之立祠于学,岁时与学官弟子拜祠焉。而记其意如此,以视邑人云。[9]
苏颂,祖籍同安,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授宿州观察推官,此后长期供职于馆阁。宋哲宗即位之初,苏颂历任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尚书右丞,元祐七年(1092)拜相。作为政治家,苏颂执政,量能授任,务使百官守法遵职;作为学者,苏颂广读传统的经史子集,在天文、历法、地理、医药、农学等古代自然科学领域更有精深的造诣。因其发明“水运仪象台”,被尊为“钟表鼻祖”,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对此给予很高评价。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乡贤,其家族后裔子弟竟茫然无知,而泉州人对曾公亮、蔡确和吕惠卿却津津乐道。有感于此,朱熹决心建苏颂祠,让更多的人了解苏颂的事迹,为学子们提供品学兼优的榜样。在朱熹看来,苏颂的可贵之处首先在于他具备士人风骨,坚守信念,做事有原则,不怕丢掉乌纱帽;其次,苏颂做学问十分专注,持之以恒,这是一般人无法办到的,特别难能可贵。
朱熹不仅主持建设苏颂祠,而且为苏颂造像。他在《奉安苏丞相画像文》中说:“惟公始终一节,出入五朝,高风耸乎士林,盛烈铭于勋府,矧兹故邑,实仰余光,怅亲炙之无从,冀瞻依之有地。是用肖德仪于庙院,建遗烈于学宫,营表方将,仪图聿至,式瞻精字,爰寓神栖,既协吉于灵辰,敢式陈于菲荐。尚飨!”[10]这篇奉安造像的祝词,以骈体文写成,措辞精美,感情充沛,反映了朱熹对苏颂的诚挚景仰,颇能鼓舞人心。
朱熹很清楚榜样的示范作用,也明白确立学习方向的重要性。为此,他先后写了《同安县谕学者》《谕诸生》《补试榜谕》《策试榜喻》,其内容包括如何为学、为教、为人父母,以及如何审问、博学的方法,非常具有针对性。
在《同安县谕学者》一文中,朱熹指出: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爱日不倦而竞尺寸之阴也。今或闻诸生晨起入学,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岂爱日之意也哉?夫学者所以为己,而士者或患贫贱,势不得学,与无所于学而已。势得学又不为、无所于学而犹不勉,是亦未尝有志于学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学不素讲也。今之世,父所以诏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学,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使古人之学止于如此,则凡可以得志于科举斯已尔。所以孜孜焉爱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后已者,果何为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为苟足以应有司之求矣,则无事乎汲汲为也。是以至于惰游而不知反,终身不能有志于学,而君子以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于上而学素讲于下,则士者固将有以用其力,而岂有不勉之患哉?熹是以于诸君之事,不欲举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诸君苟能致思于科举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为学,则将有欲罢而不能者,熹所企而望也。[11]
照朱熹的看法,凡是学习态度积极的,都能够珍惜时光。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是为学的古训,能够领悟这一古训精神者,必能发奋努力。然而,朱熹当年亲临县学时所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诸生早上来校学习,还不到中午就散去,白白浪费大半天的时间。本来,人们所担忧的是因为贫贱而没有机会学习,而入县学的生徒已经获得机会却不能勤勉,其原因何在?朱熹指出:这是由于学习目的出了问题。当时一般的人们所谓学习,都是奔着科举来的,这是为他人而学,为“有司”而学。如果古人也是为科举而学,最终不过是获得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而已,就道德生命的完善而言并没有好处。针对这种情况,朱熹强调应该“为己而士”,即为了自我生命完善,提升道德境界,成为一个真正的“士”。朱熹这种主张出于孔夫子讲的“为己之学”。《论语》记录孔子的话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对此,汉代经学家孔安国有一条注释:“为己,履道而行之也;为人,徒能言之也。”所谓“履道”就是探寻天道法则,并且遵循天道法则,进行生命自我完善的实践活动;与此相反的“为人”之学,只是学习一些华丽辞藻,停留在口头讲述阶段而已。皇侃义疏:“明今古有异也。古人所学,己未善,故学先王之道,欲以自己行之,成己而已也。今之世,学非复为补己之行阙,正是图能胜人,欲为人言己之美,非为己行不足也。”[12]
按照皇侃的理解,古人之所以能够积极主动学习,是因为明白自己有所不足,所以能够发奋而学,但后世却背离了这种学习方向。朱熹提出“为己而士”,正是为了回归学习的本来意图。从生命完善的立场看,倡导回归,既是纠偏,也是守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学”与“为教”密不可分。要让“为学”者确立生命自我完善的方向,还需要“为教”的引导。所谓“为教”,既指如何当好一名合格的教师,也指教育机构如何进行适当的管理。在这个方面,朱熹认为也应该有所总结,形成具有指导性的纲要。其所撰《谕诸职事》称:
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夫理义不足以悦其心,而区区于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犹决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萧苇以捍其冲流也,亦必不胜矣。
诸生蒙被教养之日久矣,而行谊不能有以信于人,岂专法制之不善哉?亦诸君子未尝以礼义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从,则学者之罪。苟为未尝有以开导教率之,则彼亦何所趋而兴于行哉?故今增修讲问之法,诸君子其专心致思,务有以渐摩之,无牵于章句,无滞于旧闻,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诚意于饮食起居之间,而由之以入于圣贤之域,不但为举子而已,岂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后者,亦既议而起之矣。惟诸君子相与坚守而力持之,使义理有以博其心,规矩有以约其外。如是而学者犹有不率,风俗犹有不厚,则非有司之罪。惟诸君留意。[13]
就一般的学校管理而言,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如何建立规章制度。管理者依据规章制度来约束学生的行为,倘若学生触犯规章制度,就给予相应的惩罚。然而,朱熹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建立规章制度其实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把规章制度赖以建立的理由和意义讲清楚,让受教者心服口服。如果仅仅靠规章制度企图防止学子们出错,就像用羽毛、芦苇叶子来阻拦千仞瀑布、滚滚激流一样,实际上无济于事。生徒来县学受教育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为什么不能做到取信于人、发奋努力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规章制度不完善吗?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考究起来还在于各位为师者没有从礼义上给予教导。如果已经给予教导但生徒却不遵循,那是生徒的问题;如果为师者不对生徒进行教导,那么生徒们如何落实于行动呢?这些追问,表现了朱熹对教育深层次问题的关切。为了教导生徒明白学习的根本目的,朱熹提出了“讲问”之法。所谓“讲问”就是以问答的方式学习礼义,做到循序渐进,而不是拘泥于章句和陈旧认知,而应该让“为己之学”的精神落实到饮食起居之中,做到时时刻刻诚心正意,进入圣贤的思想境界,而不是单纯为了科举考试而已。当然,朱熹没有否认建立规章制度的必要性,更不是主张抛开规章制度,而是强调通过“讲问”而让生徒真正明白规章制度的学理依据。如此,则使生徒既能在内心上认识规章制度建立的“所以然”,也能在行动上自然而然地自我约束。朱熹这种讲问方式是针对当时县学出现的问题提出来的,具有革新时弊的效能。
再进一步考察,朱熹深刻认识到教育乃是代代相续的事情,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必须一以贯之。其《补试榜谕》谓:
盖闻君子之学以诚其身,非直为观听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风俗所以淳厚而德业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学小生,自为儿童时,习见其父兄之诲如此,因恬不以为愧,而安受其空虚无实之名,内以傲其父兄,外以骄其闾里,终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归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劝谕县之父兄,有爱其子弟之心者,其为求明师良友,使之究义理之指归,而习为孝弟驯谨之行,以诚其身而已,禄爵之不至,名誉之不闻,非所忧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务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贻终己之羞哉?今兹试补县学弟子员,属熹典领,故兹劝谕,各宜知悉。[14]
这篇《补试榜谕》,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关联起来考虑,从整体上把握教育各个环节的关联性与统一性,其着眼点从“为己之学”提升到“君子之学”。
在古人心目中,“君子”是一种道德理想典型。《周易·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言》解释《乾》卦之“元亨利贞”时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15]所谓“元亨利贞”,在《周易》中代表春夏秋冬周而复始的自然秩序,其所体现的是天道自然法则。君子格物致知,观物取象,当以“诚”为本。《中庸》有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16]在儒家看来,“诚”是一种天性,而“诚之者”是说通过学习而合于天道本性,这就是“天人合一”。朱熹汲取传统经学的精神,认为君子做学问就在于一个“诚”字。自己修身养性要“诚”,教育弟子也同样遵循“诚”的原则,如此而形成敦厚的社会风俗和崇高的德业。
然而,世风日下。曾几何时,社会上慢慢出现一种坏风气,为人之父母者,失去了诚信,“假手程文”,因袭前人科举考试所留下的所谓“范例”,弄虚作假,习以为常。孩子们从小在这种环境中接受虚伪风气的浸染,养成了浮华的学风与傲慢的坏脾气,于是终身不能自力更生,这是多么可悲的情状啊!有鉴于此,朱熹大声疾呼,希望本县的父兄,基于慈爱子弟的内心情感,寻找良师益友,让弟子们深入思考义理精神,进行孝悌的道德实践,真正做到“诚其身”,至于功名利禄之事并不应是家教首先需要忧虑的。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朱熹针对原有县学的诸多问题,形成了新的论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反对单纯的科举应试教育,而倡导以品德教育优先,把素质教育、人格完善教育与知识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了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的系统工程教育思路。正是这种思路,改变了当时存在的诸多弊端,也由于这种思路,当时的县学完善起来(修建经史阁,整理县学存书,聘任乡贤柯国材进士等诸多学者任教),传承礼义之学蔚然成风,一时从学者众。根据《同安县志》《泉州府志》《闽中理学渊源考》等文献资料记载,朱熹在世时,闽南已形成了朱子学派,而同安县学即该学派的发源地。
四、解经明道,归体以立正
朱熹在同安当主簿,当时他的生活条件并不好,甚至有点拮据。其安处的主簿廨,“皆老屋支拄,殆不可居,独西北隅一轩为亢爽可喜,意前人为之,以待夫治簿书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视其所以名,则若有不屑居之之意”[17]。对于这样的简陋住处,朱熹善于自嘲,苦中作乐,他“亢爽”地将此“主簿廨”更名为“高士轩”,并且制了一块大匾郑重其事地挂上。这当然不是“自视其高”,而是用以引高人来相会。他在所撰《高士轩记》中说:“夫士,诚非有意于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独立乎万物之表者,亦岂有待于外而后高耶?知此,则知主县簿者,虽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轩虽陋,高士者亦或有时而来也。顾予不足以当之,其有待于后之君子云尔。”[18]如此果然奏效,先前令人“不屑”的小屋于牌匾挂出之后竟然引来高朋满座。南宋李幼武撰《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二记载:朱子“莅职勤敏,纤悉必亲,廨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轩’,而以令甲凡簿所当为者,大书揭之楣间,职兼学事,身率诸生,厉以诚敬,开以义理,皆竦慕而师尊之”[19]。明代戴铣辑《朱子实纪》评述:朱熹于此高士轩解经论理,“身率诸生,规矩甚严厉,以诚敬闻,以义理初,士子尚循”[20]。陆应阳《广舆记》称:“朱熹主同安县簿,建高士轩,集诸弟子,朝夕讲学其下。”[21]由此看来,此高士轩虽然破旧不堪,却能吸引众多学者前来听讲,相互切磋,令人敬佩。
《闽中理学渊源考》说:
朱子临莅同安,阐明圣学,崇奖名教,泉之学士斌斌向风矣。厥后,陈后之、刘叔文、杨至之、许顺之,亲承言论;蔡白石、陈北溪,递衍师说,与吕朴乡、丘吉甫,后先辈出,时谓之清源别派,志乘载考亭道脉,传入温陵,所著录者二十余人。[22]
这段记载所罗列的生徒虽然来源较广,但以同安作为汇聚的中心点,而后再度传播,形成了“清源别派”,蔚为大观。
《闽中理学渊源考》又说:
紫阳文公门徒,惟同安诸生受业最早,有柯国材翰、许顺之升、陈氏齐仲、徐氏元聘诸先生。考文公与国材书云:“戴陈二生,趣向文辞,皆可观,固知其所自矣。有友如此,足以为仁,敢以为足下贺,而仆亦将有赖焉。”又云:“某自延平逝去,学问无分寸之进,汩汩度日,无朋友之助,未知终何所归宿”云云。又曰:“李君好学礼贤,其志可嘉,国材想亦推诚与之讲论,有可采处,若得同为此来,真寡陋之幸。”[23]
《闽中理学渊源考》有柯国材的简明传记,谓其为同安人,名翰,字国材,进士出身。朱熹任职同安主簿,“属治学事,引翰自助,翰内行峻洁,众严惮之,久皆化服,葺庐以居”,柯国材取扬雄“三年通一经”之言,作为讲学场所的名称,朱熹特地为此写了《一经堂记》。其略云:
予闻古之所谓学者非他,耕且养而已矣。其所以不已乎经者,何也?曰: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学始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则意诚心正,而《大学》之序推而达之无难矣。若此者,世亦徒知其从事于章句诵说之间,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固将以为耕且养者资也。夫岂用力于外哉?柯君名翰,字国材,为人孝谨诚悫,介然有以自守,于经无不学,今将隐矣,而其志不自足如此,是盖终身焉,则其造诣之极,非予所敢量也,姑次比是说为之记云。[24]
行文显得颇为谦恭,这是因为柯国材虽然在职务上是朱熹的助手,但却年长14岁,所以朱熹对他特别敬重,以兄长相待。其中言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经论,颇有来历。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奉命任主簿于同安,兼管县学。翌年,朱熹知遇柯国材,遂成忘年之交。当时,县学缺少直学(掌管钱谷)一职,朱熹发函聘任之。《举柯翰状》称:“窃见进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随流俗,专以讲究经旨为务,行年五十,亹亹不倦,置之学校,必能率励生徒,兴于义理之学,少变奔竞薄恶之风,欲乞备申使府,差补施行。”[25]南宋同安县学司书兼奉文公祠陈利用编的《大同集》载:国材讲《礼记》,朱子申其说,反复辨论《仁体》《忠恕》《易卦》《春秋》等。[26]这些资料显示,朱熹与柯国材的讨论,乃是以儒家传统经学为核心展开的,这一点从后来朱熹回复柯国材的四封信函可以得到佐证。这些书信,讨论最多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周易》,可以看出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以及《周易本义》的雏形。
在经学诠释问题上,朱熹对朋友或同安生徒的书信回复,绝不拐弯抹角,而是直抒其意。且看他回复柯国材的一封信:
示谕忠恕之说甚详,旧说似是如此,近因详看明道、上蔡诸公之说,却觉旧有病。盖须认得忠恕便是道之全体,忠体而恕用,然后“一贯”之语,方有落处。若言恕乃一贯发出,又却差了此意也。如未深晓,且以明道、上蔡之语思之,反复玩味,当自见之,不可以迫急之心求之。如所引“忠恕笃钦”以下,尤不干事,彼盖各言入道之门、求仁之方耳,与圣人之忠恕道体本然处,初不相干也。一阴一阳,不记旧说,若如所示即亦是谬妄之说,不知当时如何敢胡说,今更不须理会,但看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即是道之全体,非道之外别有道也。[27]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收录《答柯国材》的回函共有四封,此处所引系第四封的开头一段,讨论的基本议题是“忠恕之道”与先天图。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如何理解“忠恕”问题,朱熹认为“忠恕”乃是“道之全体”,他从“体用”两个层面诠释“忠恕”的关系,“忠”是“体”,而“恕”为“用”,此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二是敢于承认错误与修正观点。例如关于“一阴一阳”的解说,柯国材将昔日的记录拿出来与朱熹讨论,朱熹细想之后觉得以前的讲述是“胡说”,大抵是课堂上的即兴发挥。而今回信,明确表示不要理会以前的错误说法,而以“道之全体”作为把握的方向。这种敢于承认错误、修正观点的做法,体现了闽学一开始就具有实事求是的严谨特质,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认真继承的。
明代理学家林希元曾于《重刊〈大同集〉序》中追溯朱熹于同安传道授业的情形。
是时年方二十有四,尚在志学之日,然其所为文字已如老成人,其教人无非格言至论,其与诸生辨疑解惑,皆有以发前圣之微旨,足为后学之印正,虽其晩年所就,曾不能大有加于旧,庸是见考亭之学,其得于天者,夐异诸人。[28]
照林希元的说法,朱熹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其文字已经相当老到,他善于用格言至论来启迪生徒,其立论讲述处处引经据典,堪为后世楷模。林希元为之作序的《大同集》收录了朱熹任同安主簿时所作的诗、书、序、记、跋、杂著、行状等文章,以及朱熹离开同安后所作的与同安的人、事、地有关的著述。对照品读,我们可以更加深切地把握闽学源头在同安的历史脉络。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朱熹任职同安主簿,兼管县学教育,他不辞劳苦,勤政为民,以俭自律,以朴致廉。他走遍同安的东南西北,领略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同安秀丽的自然环境与敦厚的人文环境,陶冶了朱熹的性情,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同安县学与曾经破旧不堪的“主簿廨”在他别出心裁的改造下,成为他收徒授业、解经明道的神圣舞台。“化腐朽为神奇”的哲匠理路与“点石成金”的笔法,让其生活起居的时空都打上了传承经学、发展经学、移风易俗、建立学派的文化烙印。他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与敏锐的鉴赏目光,善于发现人才与培育人才。朱熹于同安任职尽管只有四年时间,但把教育事业做得有声有色,而他的文化助手与培育出来的一大批门徒也都尽心尽力,乐于耕耘,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文化建树。这笔珍贵的精神遗产锻铸了同安的文化之魂,也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视野下的中华生命智慧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A082)阶段性成果。
[1] 朱熹:《观书有感二首》(其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四部丛刊》明嘉靖刻本。
[2] 朱熹:《观书有感二首》(其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四部丛刊》明嘉靖刻本。
[3] 朱熹:《答许顺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四部丛刊》明嘉靖刻本。
[4] 李清馥:《许顺之先生升》,《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六,《稗海》本。
[6] 熊节编:《观诗》,熊刚大句解:《性理群书句解》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四部丛刊》明嘉靖本。
[8] 何晏集解:《述而第七》,《论语集解》卷三,《四部丛刊》日本正平本。
[9] 朱熹:《苏丞相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四部丛刊》明嘉靖刻本。
[10] 朱熹:《奉安苏丞相画像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六,《四部丛刊》明嘉靖刻本。
[11] 朱熹:《同安县谕学者》,《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四部丛刊》明嘉靖刻本。
[12] 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七,清长塘鲍氏刻本。
[13] 朱熹:《谕诸职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四部丛刊》明嘉靖刻本。
[14] 朱熹:《补试榜谕》,《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四部丛刊》明嘉靖刻本。
[15] 卜商:《子夏易传》卷一,《通志堂经解》本。
[16]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五十三,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十三经注疏》本。
[17] 朱熹:《高士轩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四部丛刊》明嘉靖刻本。
[18] 朱熹:《高士轩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四部丛刊》明嘉靖刻本。
[19] 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戴铣辑:《朱子实纪》卷二,明正德八年鲍雄刻本。
[21] 陆应阳:《广舆记》卷十八,清康熙刻本。
[22] 李清馥:《朱子泉州门人并交友》,《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李清馥:《朱子泉州门人并交友》,《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 朱熹:《一经堂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四部丛刊》明嘉靖刻本。
[25] 朱熹:《举柯翰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部丛刊》明嘉靖刻本。
[26] 参见陈笃彬、苏黎明:《泉州古代教育》,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66—67页。
[27] 朱熹:《答柯国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四部丛刊》明嘉靖刻本。
[28] 林希元:《重刊〈大同集〉序》,《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七,清乾隆十八年陈胪声诒燕堂刻本。
- 编辑: 张益豪
- 统筹: 侯绍华 李沅栗
- 编审: 翟 佳 周之江
